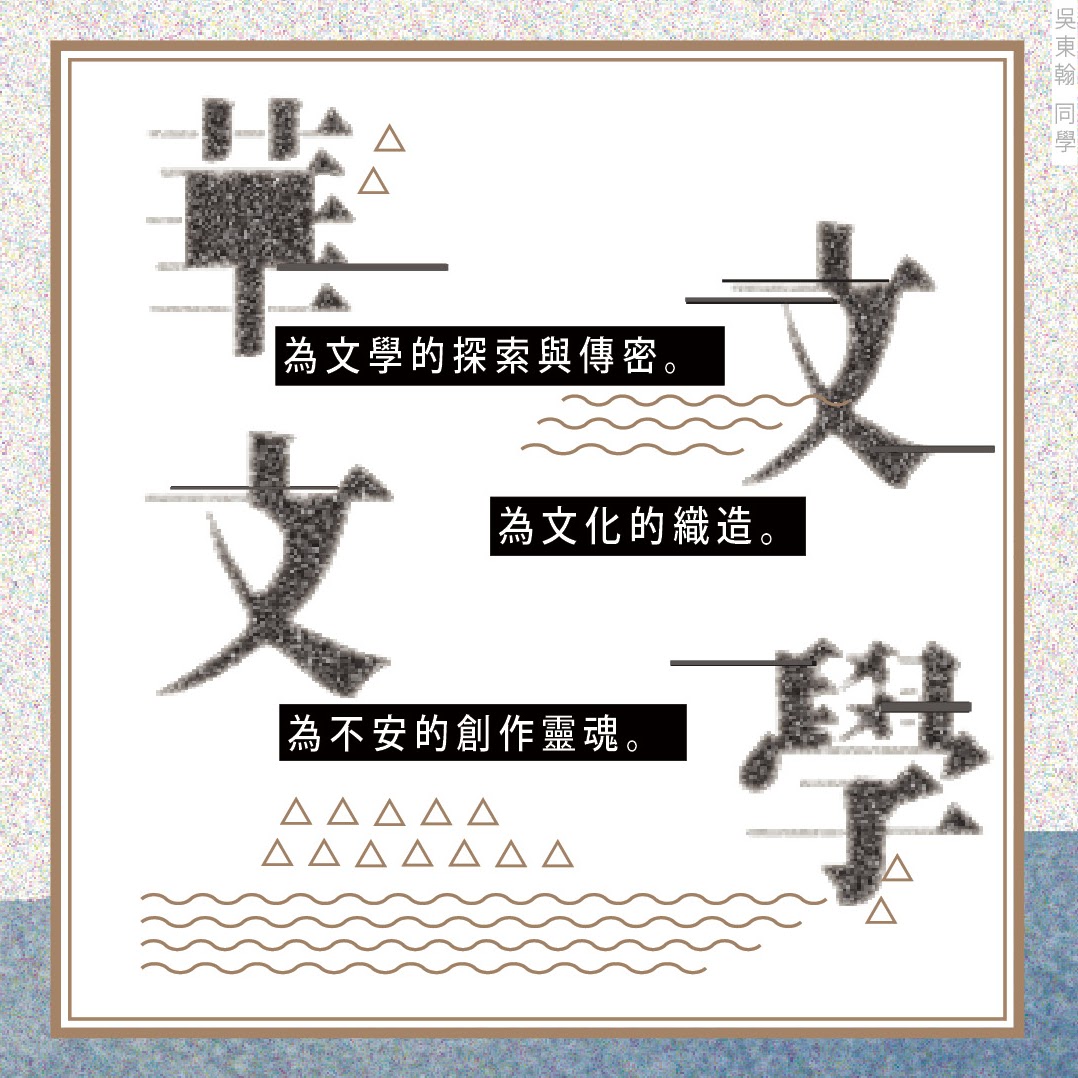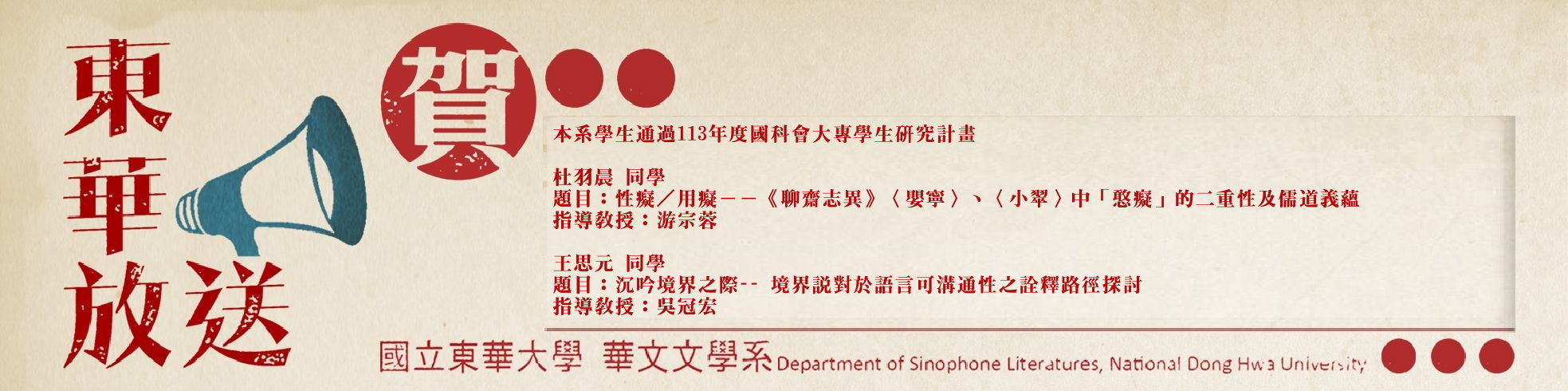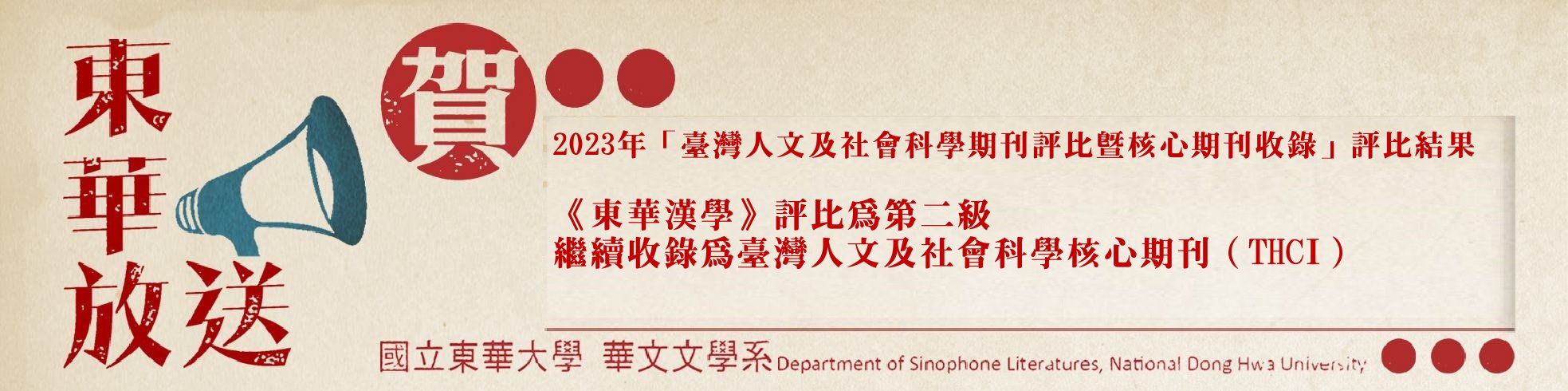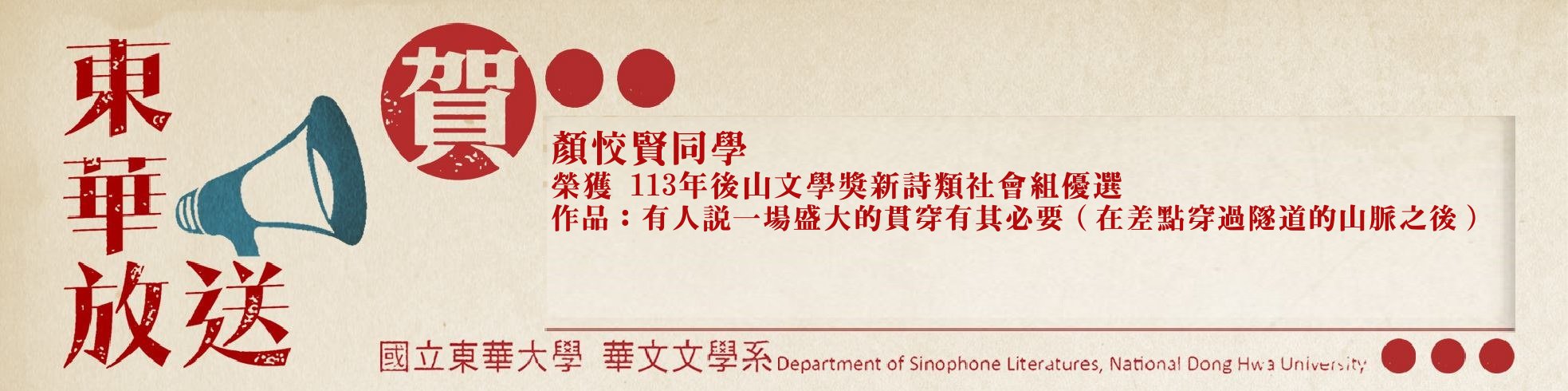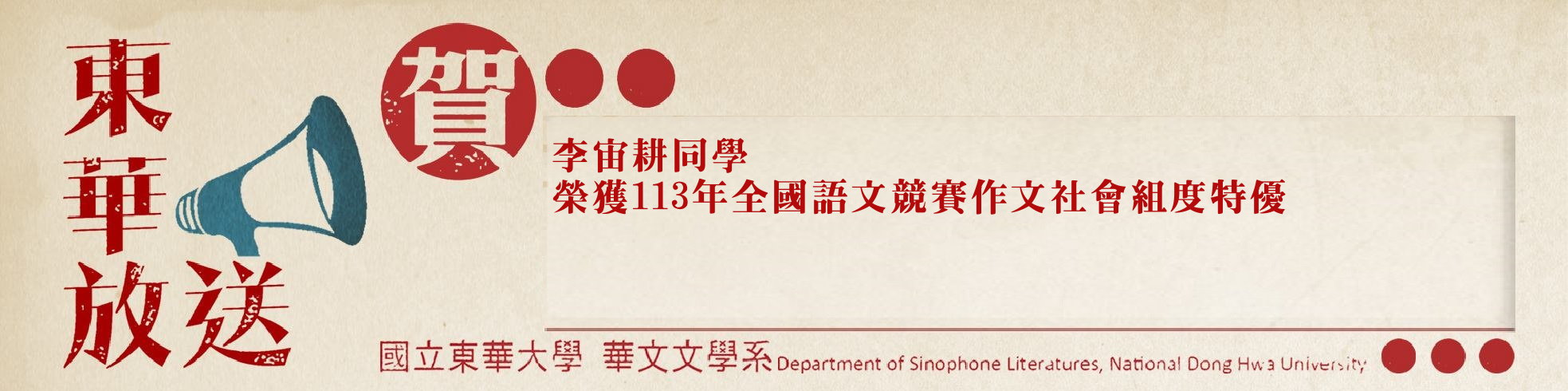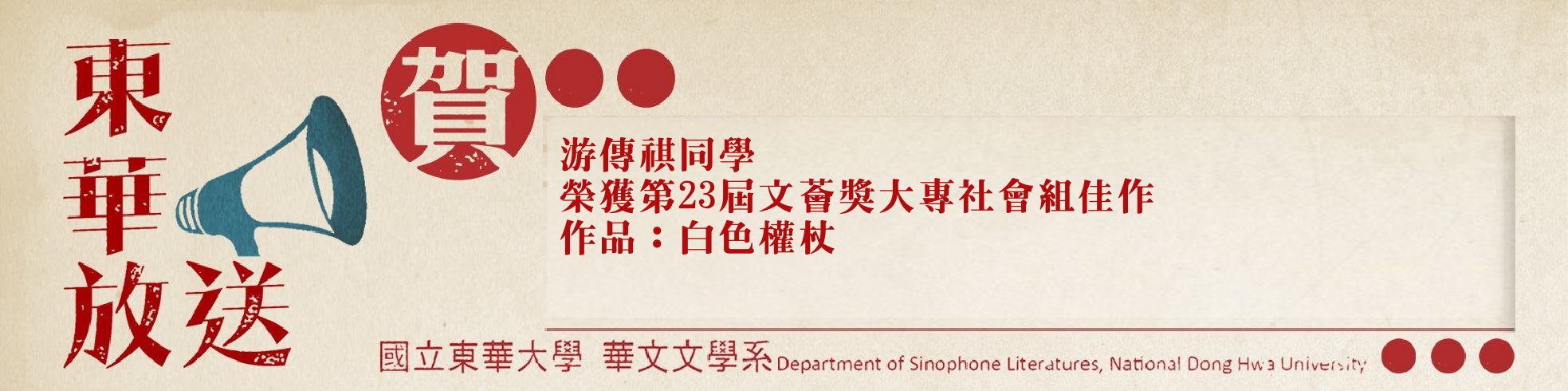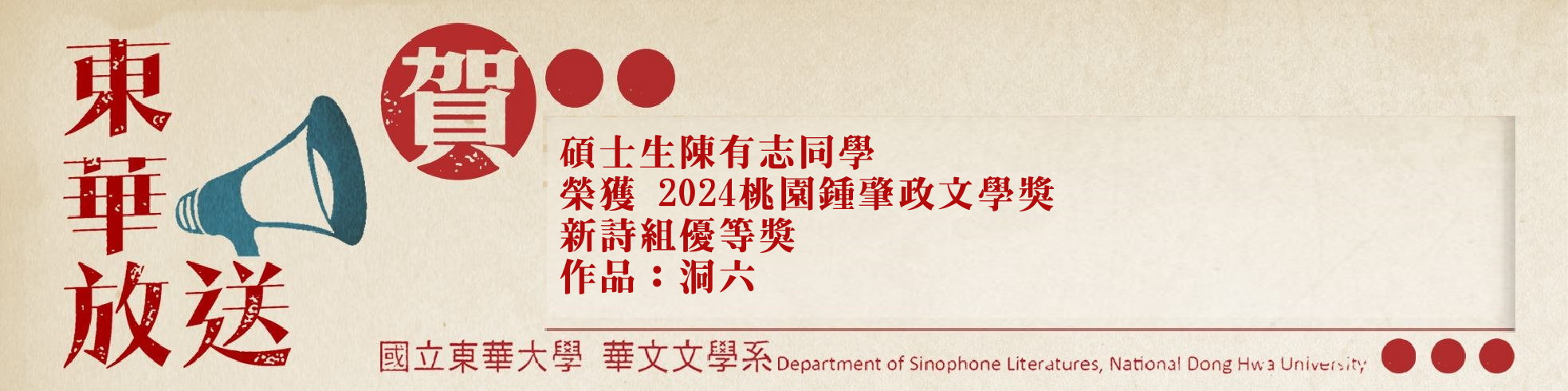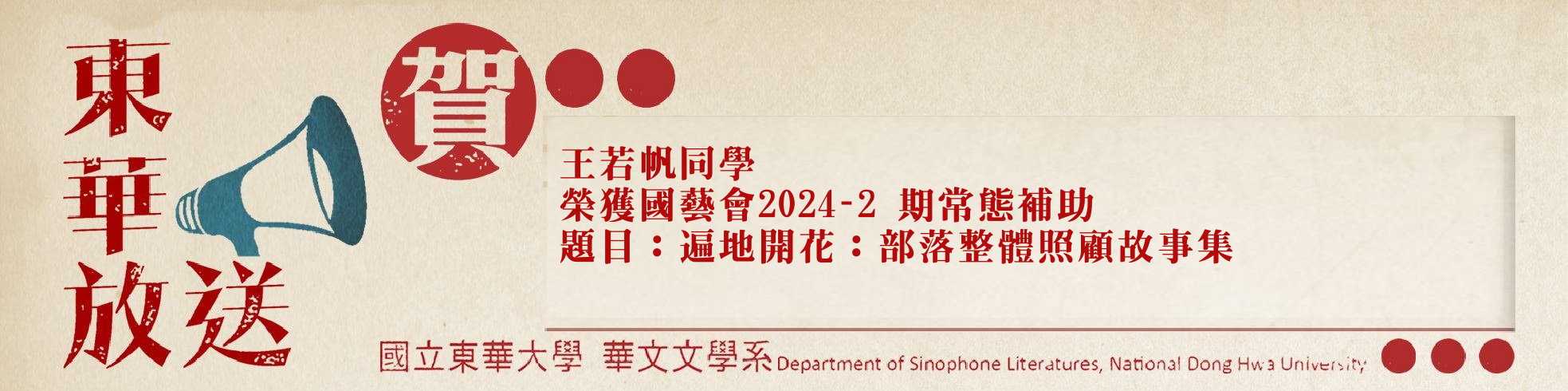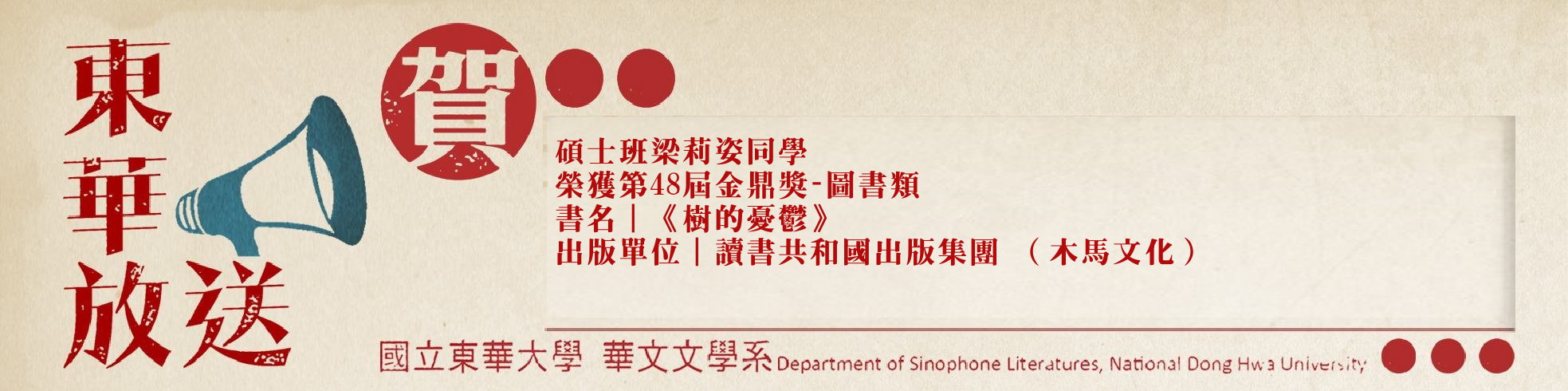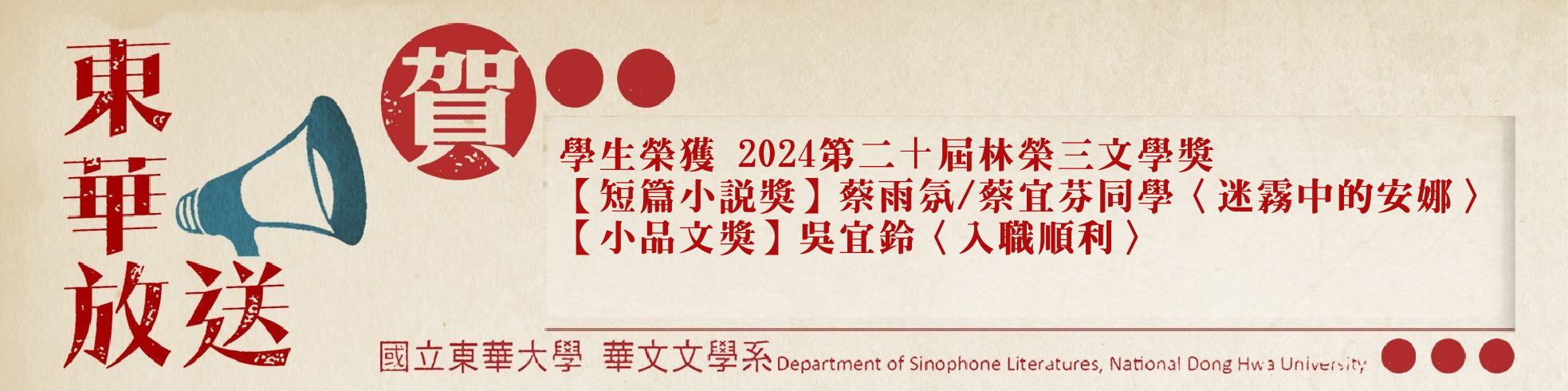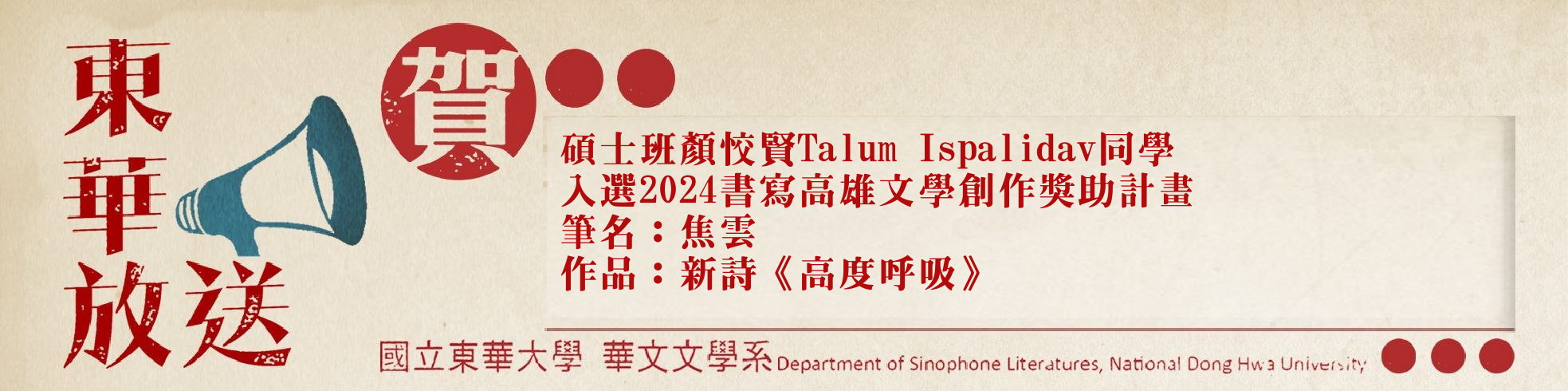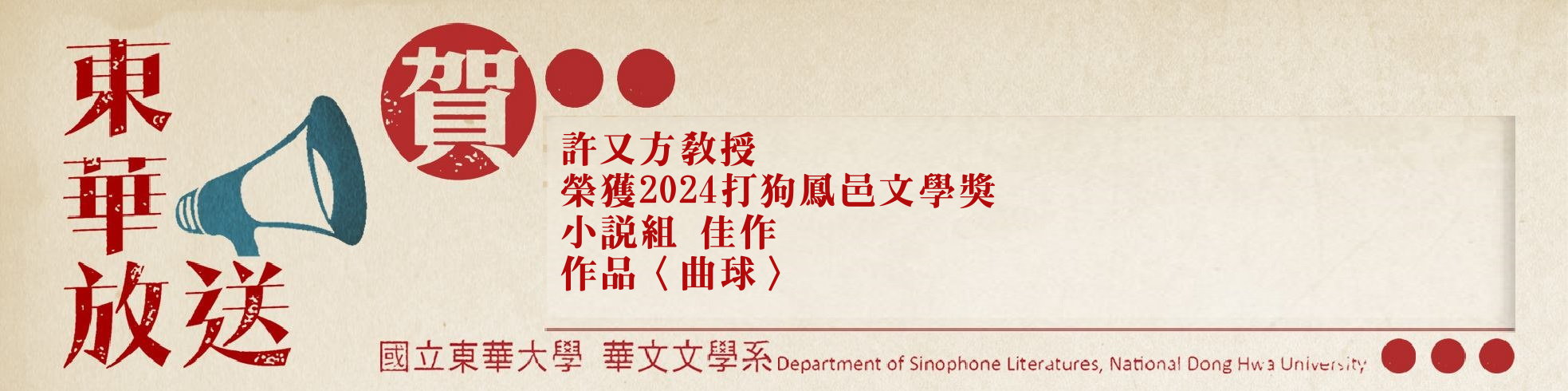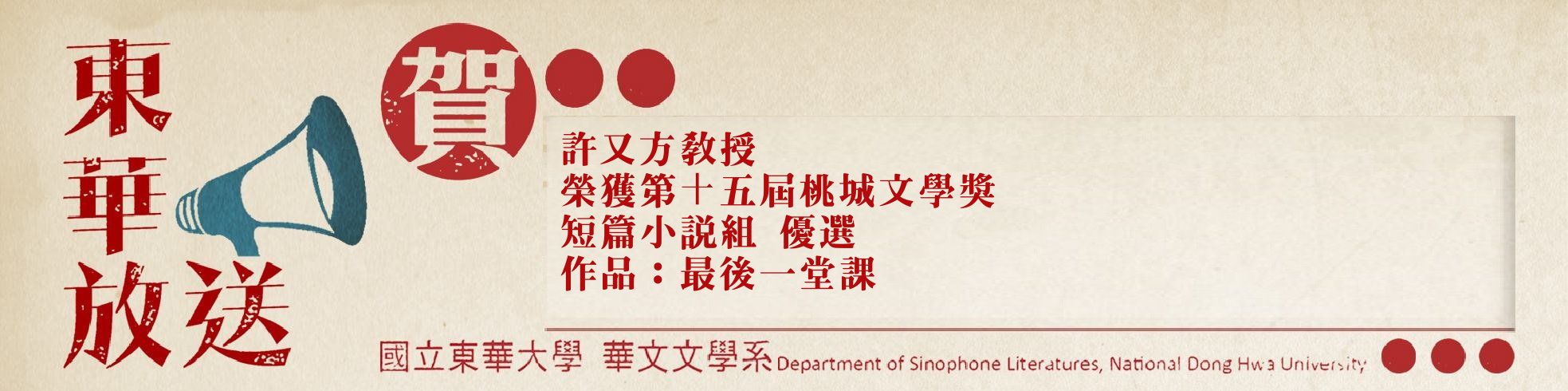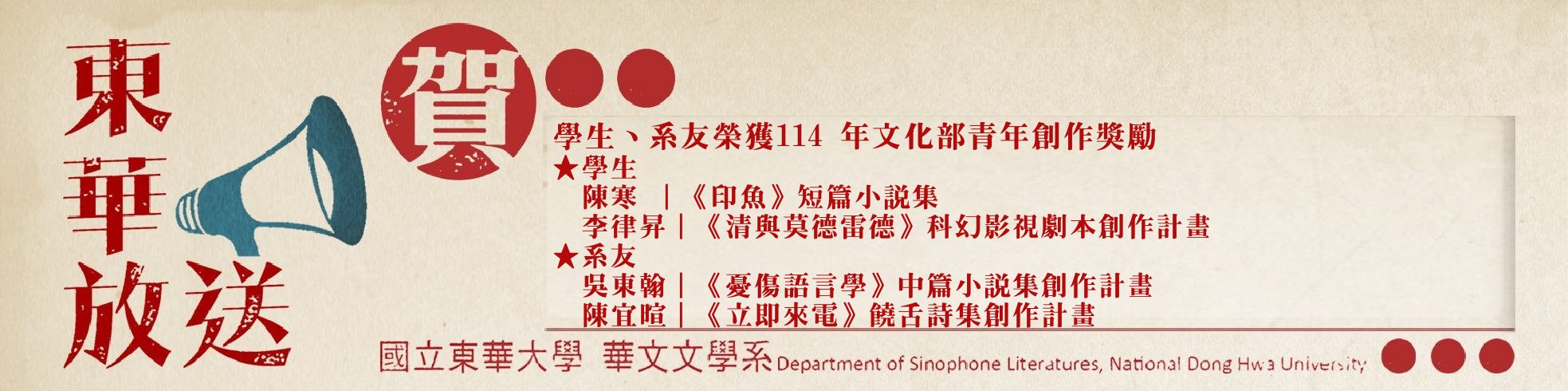【關於馬華文學】〈在台馬華文學〉《馬華文學》∣張錦忠
在台馬華文學
張錦忠《馬華文學》
馬華文學一向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在」馬來西亞生產的華文文學。但是,馬華文學的生產場所也有可能「不在」馬來西亞,而在例如台灣、香港等境外地區。在台灣發生的馬華文學現象,過去較常看到的稱謂是「馬華旅台文學」。近年來,「在台馬華文學」的用法較為多見。廣義而言,「在台馬華文學」不一定限於馬華作者在台,也指「馬華文學」在台,即作品在台灣出版流通。
早在一九六○年初期,「在台馬華文學」已經在台灣冒現。當時留學台灣的華裔馬來西亞學生如黃懷雲、劉祺裕、張寒等就已積極參與台灣文壇活動, 在這裡結社、出書。換句話說,「在台馬華文學」其實就是馬華留台生在台灣的文學表現。
早期馬華留台生的文學表現與活動比較為人所知的例子,則是一九六三年成立的星座詩社。星座詩社是一個跨校園性質的文學團體, 雖然未自我標榜為「僑生」社團,但是主要成員包括王潤華、淡瑩、翱翱(張錯)、黃德偉、畢洛、林綠、陳慧樺(陳鵬翔)等馬來西亞與港澳「僑生」。星座創社初期,獲得台灣詩人李莎和藍采的支持甚多。藍采是《星座詩刊》創刊號編者,〈代發刊詞〉即出自其手筆。成立第二年後,詩社開始出版詩刊與叢書。一九六九年詩刊停止出版,象徵星座停止發光。一九七二年,星座若干成員重組,陳慧樺、余中生、李弦(李豐懋)、陳芳明、林鋒雄等成立大地詩社,出版《大地詩刊》、《大地文學》,出版活動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二年。[1]
一九七四年底,天狼星詩社的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周清嘯等人跨海來台升學,並在台北出版《天狼星詩刊》,一九七六初與天狼星詩社決裂,另組神州詩社。溫瑞安、方娥真等人除了出版《神州詩刊》之外,也由時報、四季、長河、皇冠、源成等出版社刊行的詩集、小說集、散文集、合集(《神州文集》)與武俠小說等多種。神州詩社在後期改稱神州社,同人並在一九七九年另組青年中國雜誌社,出版《青年中國雜誌》,鼓吹「文化中國」的理念。神州社員多達百人以上,除了溫方等人之外,都是台灣本地青年。
我們不妨這麼說,星座詩社(及大地詩社)與神州詩社分別代表了一九六、七○年代留台「僑生」或離散華裔文藝青年追求與認同「中華屬性」的兩種模式。台灣在那些年代,以「中國」或「自由中國」自居。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中國國民黨光復台灣。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退台灣,在台澎金馬延續「中華民國」的政體,直到今天。國民政府遷台以後仍然以「中國」自居,突顯的是其大中國意識形態。依照這樣的意識形態,在台灣生產與出版的華文文學文本乃是「中國文學」,現代詩則為「中國現代詩」,神州社溫瑞安也慷慨激昂地說,「為中國做點事」。換句話說,在冷戰的年代,台灣以「中華屬性」的代言者自居,而在各個公共領域所論述的「中國」,乃「中華屬性」的符號,而非地理政治實體。因此,即使在中國開始積極在國際舞台冒現的七○年代,台灣文壇還是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大系》(1972)、《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1977)這類企圖打造「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典律的書。
在六、七○年代的台灣文化的當道論述中,發生在台灣的文學表現被自我表述為「中國文學」。因此在台的離散華語系作家如王潤華等人在台灣成立星座詩社,或後來陳鵬翔等人成立大地詩社,作為他們在台灣的書寫活動基地,也表示他們認同台灣的「中國文學」文化或文化政治符號意涵。這個「中國認同」的文化政治符號,顯然是冷戰時代的產物。誠如陳鵬翔所說,他們詩作中「所展現的疏離、孤獨等……主要是思鄉、寂寞,更大程度,還是受到當時宰制文化(反共文學vs.現代派、存在主義)與社會風氣的感染」(陳鵬翔2001:121)。這個宰制文化背後的意識形態,可視之為「中國認同」或「中華屬性中心論」。
但是,儘管以星座成員中諸馬華詩人為代表的在台馬華文學向這個「中國認同」或中華屬性中心論靠攏,積極參加六○年代的文學活動,在台灣文學複系統位居中央的當道者或主流論述眼中,他們很可能「不夠中國」。例如,一九七二年,巨人出版社推出一套八冊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分詩、散文、小說卷,選錄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二十年間在台灣生產的作品,為當年相當重要的典律建構。這套大系由余光中、洛夫、朱西甯、張曉風等九人組成編輯委員會,其中詩卷二冊,由洛夫與白萩編選,共收入七十位詩人的作品,令人意外的是,星座詩人竟然沒有一人上榜。
事實上,當時星座詩社同仁中至少林綠、王潤華、翱翱、陳慧樺與淡瑩五人在台灣詩壇的表現已卓然出色。林綠在六○年代中葉已相當活躍,其他人如王潤華與翱翱,作品早已入選一九六七年出版的《七十年代詩選》,稍早出版的《大學生詩選》(1965)也收入王潤華作品,一九七一年張默與管管編選《新銳的聲音:當代廿五位青年詩人作品集》(1975),也選入陳慧樺、鍾玲、蘇凌的詩作,表示星座詩人的文學表現已獲得相當的肯定,至少不是那麼邊緣。但是在巨人版《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選卷編者的「中國文學」典律建置工程中,星座詩人並未列名其間,那顯然是文學政治操作的結果。
溫瑞安、方娥真等神州詩社馬華成員追求與認同「中華屬性」的模式,由於時代氛圍不同,有別於星座詩社回歸華文文學主流的「中國認同」。對溫瑞安等人來說,「中國文學」等同「中國」。文學成為想像中國或慰藉文化鄉愁的方式。換句話說,文學取代了現實政治與地理實體,成為神州同仁「想像中國」的管道或空間。就像夏志清在論余光中的文章所說的,余光中「所嚮往的中國並不是台灣,也不是共黨統治下的大陸,而是唐詩中洋溢著『菊香與蘭香』的中國」(夏志清 1979:388-89)。這句話借來描述神州詩社在台灣的中國認同最適合不過。
上面提到時代氛圍不同,指的是時序到了一九七○年代,台灣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早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國際政治現實逼使台灣不得不放棄(或被迫失去)想像中國的空間,加上海外保衛釣魚台運動的發酵,本土主義(包括鄉土文學運動與本土政治運動)和民族主義興起,在在促使生活在大陸邊陲與外海島嶼的各省籍台灣人正視現實,重新「發現台灣」,反思中國傳統文化,漸漸無法藉唐詩宋詞或六○年代現代詩等「中國文學」想像或迷思「中國」,甚至「三民主義反攻大陸」也漸漸成為淹沒在時代洪流的口號。一旦《山河錄》中的假山假水無法滿足這種逐漸被現實戳破的「中國想像」時,溫瑞安只好埋首武俠小說來神遊「文化中國」。
溫瑞安所觀望與想像的世界是「文化中國」而非台灣,更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對非馬來人的種族分化政策,對華人文化、教育與文學的漠視或邊緣化,造成華人文化危機意識。溫瑞安在散文與詩中對華人的這種困境頗多譬喻與敘述。他在第一本詩集《將軍令》跋文寫道:「我們總不能、總不能看見這頭受傷的蒼龍,絕滅在我們這一代的手裡」(溫瑞安1974:42)。但是在「龍哭千里」的馬來西亞,要以華文文學實現「文化中國」的理想,溫瑞安認為「此乃是非地,而非風雲密佈之中原,在此只有金劍沉埋」(溫瑞安1974:43)。這是溫方等人決心在一九七三年離馬赴台的原因。
但是,說溫瑞安與神州社核心份子昧於現實,只活在想像的世界裡,也並不公平。他們在旅台期間也常返馬。當時馬來西亞與中國也已建立邦交,中國歌曲、影片與書刊在馬來西亞也算通行,他們不可能視而不見。文革終結前後的中國,百廢待興,當然不是溫瑞安所想像與建構的「文化中國」,但也不是一無可取的廢墟。日後成為溫瑞安與方娥真「為匪宣傳」的證物中,據聞就有《劉三姐》的歌曲錄音帶。一九八一年初,溫瑞安與方娥真被台灣警備總部逮捕拘留,判刑後驅逐出境,周清嘯、黃昏星、廖雁平等社員也先後返馬,瓦解了百人結社的神州社。
一九七○年代末、八○年代初,經過了鄉土文學論戰後的台灣文壇,儘管高度現代主義文學風潮已退,鄉土文學並未獨領風騷。本土文化論述與黨外運動要等到八○年代中期以後才冒現開展。文學在這期間呼應時代社會的急速變遷,朝向多樣性發展,《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文藝副刊分別在高信疆與瘂弦的主持之下,成為文學的重要贊助者。除了副刊內容的改革外,兩大報更落實文學行動主義,舉辦文學獎,左右了文學方向,堪稱掀起「文學寧靜革命」。在《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文學獎得獎名單中,商晚筠、李永平、張貴興、潘雨桐的名字經常出現,得獎作品甚獲批評家的讚賞。四人之中,商、張、潘三人得獎之後在台灣出版了他們的第一本書,而李永平雖然早在一九七六年就已在台灣出版短篇集《拉子婦》,獲得《聯合報》文學獎之後出版的《吉陵春秋》更備受推崇,迄今仍然是華文文學經典之作。潘雨桐在五○年代末六○年代初留台,復於七○年代上半葉在台灣任教,但是他的寫作事業是在返馬後才展開,並在八○年代屢奪文學大獎。儘管商晚筠的第一本小說集《癡女阿蓮》出版時人還在台,她在七○年代中畢業後即返馬, 嚴格說來, 潘商二人只能算留台,而非在台馬華作家,但是他們的作品在台灣出版,一直是在台馬華文學重要文庫。
在台的李永平、張貴興,以及留台的商晚筠、潘雨桐等馬華作家既未如星座、大地諸人般成立同仁文社,也未再如神州社般百人結社,基本上除了李永平之外,他們從參加文學獎起家,獲得文學界認可(因此人不一定要在台。李永平得獎時人也在美國。後來的在台得獎的黎紫書既非留台也不在台,但書一直在台出版,最新一本是今年出版的小說集《簡寫》)。因此,我們不妨說,到了七○年代下半葉以後,參加兩大報及其他文學獎已取代了結社或自費出版,成為馬華作家在台灣「取得進入文壇的通行證」的途徑,也開啟了在台馬華文學的第三種存在模式,這種模式未必和追求與認同「中華屬性」有必然關係。
二、三十年來,兩大報文學獎既「為大馬留台生提供了一片不可思議的成長空間」(陳大為2001:33),提供這支陳大為稱作「外來兵團」的離散馬華書寫者一個只認作品不認人的操練場域,讓馬華文學有機會在台灣大放異彩;相對的,台灣文學複系統也不得不挪出部份空間來容納這批充滿域外風格或異國情調的文本 。九○年代以後,在台馬華作家如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林辛謙(後來移居香港),也是透過文學獎取得在台文學身分,晚近的辛金順也是如此。留學台灣等於是他們的文學成長儀式之旅。
和文學獎一樣,選集也是一文學系統中典律建構的重要工程。拜兩大報文學獎之賜,七、八○年代以來,這批得獎作家的作品也入選各種年度詩文選集,儘管入選比例不算特高,例如《九十年代詩選》只收入陳大為與陳慧樺兩位馬華詩人。另一方面,和以往馬華旅台作家期待被各選集編者青睞的被動心態不同的是,九○年代旅台馬華作家主動出擊,在台灣出版、編選各文類的馬華文學選集,達到自我建構典律的功效,也將當代馬華文學風貌展現在台灣讀者面前,提高了馬華文學在台灣的能見度。一九九五年,陳大為率先編了《馬華當代詩選(1990-1994)》,第二年鍾怡雯編輯《馬華當代散文選(1990-1995)》,黃錦樹在一九九八年主編《一水天涯:馬華當代小說選》,而陳大為與鍾怡雯於二○○○年合編的《赤道形聲:馬華文學讀本I》更是典律建構大工程。《中外文學》也在二○○○年九月號推出我客座編輯的《馬華文學專號》,內容包括論述、創作、書目與訪問。二○○四年,我編輯《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收入在台灣舉辦的第一個馬華文學研討會相關論文多篇;同年黃錦樹和我主編《別再提起:馬華當代小說選》,收入一九九七年至二○○三年間發表的馬華小說代表作。我們原本還打算在台灣推出一本題為「華馬小說七十年」的選集,收入華裔馬來西亞作者以不同語文書寫的小說,可惜後來出版社因市場考量放棄此出版計畫。近年來陳大為與鍾怡雯在台推廣馬華文學更是不遺餘力,先是 於二○○四年續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II》,二○○七年編選《馬華散文史讀本1957-2007》三卷,更於二○○八年將四年前建構的「馬華文學評論數據庫」擴大為「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http://ctwei. com/mahua)。
除了上述三種模式之外,在台馬華文學還有另一種存在模式,這第四種模式通常為論者所忽略。一九八三年,馬來西亞留台學生在台北出版《大馬新聞雜誌》,關心國是,批評時政,試圖建立大馬華裔青年的「馬來西亞論壇」。次年,大馬青年社成立,出版《大馬青年》雜誌,標榜馬來西亞意識,並接辦大馬旅台文學獎。在此之前,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的台北總會出版機關報紙《會訊》也行之有年,裡頭設有文藝欄。《大馬新聞雜誌》除了雜誌外,也出版「大馬新聞雜誌文學性叢書」多種,其中包括陳強華詩集《化裝舞會》。陳強華來台前已在馬來西亞出版了第一本詩集《煙雨月》,大一那年獲得政治大學長廊詩社的詩獎,後來出掌詩社,主編《長廊詩刊》,致力推動校園詩運,畢業返馬後在檳州大山腳創辦「魔鬼俱樂部」詩社。此外,大馬新聞雜誌社也出版了羅正文與傅承得的詩集。羅正文跟李永平、張貴興一樣,來自砂拉越,留台時出版了詩集《臨流的再生》及兩本被馬來西亞政府查禁的政論書,返馬後任《星洲日報》主筆。傅承得的《哭城傳奇》預告了他下一本重要詩集《趕在風雨之前》的政治抒情基調。傅陳二人留台期間也曾經獲得大馬旅台文學獎。
與《大馬新聞雜誌》、《大馬青年》一樣,大馬旅台文學獎也是大馬留台同學的重要文學活動場域。這個文學獎曾經是黃錦樹、陳大為、與鍾怡雯在九○年代初練筆的操場,也是擔任評審的台灣作家學者接觸馬華文學的管道。不過,近年來大馬旅台文學獎和《大馬青年》辦辦停停。我看到的最新一期《大馬青年》是二○○五年出版的第十二期,主編為吳子文,在台灣大學外文所念碩士班,書由唐山出版社出版。這期《大馬青年》刊載了第十二屆大馬旅台文學獎作品,還有「旅台馬華文學」發展概述。不過,這一期雜誌離第十一期的出版日期,已隔了五年之久。
這批留台生在這裡編雜誌、辦文學獎、出書、舉辦演講,台北簡直就是一個在馬來西亞境外活動的場域。《大馬青年》第七、八期編者便曾以馬華旅台文學為焦點,製作「旅台文學史料」專輯,肯定了旅台文學在馬華文學史中的重要位置。黃錦樹的〈「旅台文學特區」的意義探究〉一文即此旅台文學史料收集的工作成果。後來他的長篇論文〈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也可視為那兩期《大馬青年》未竟之業的延續。那兩期編者之舉,其實早已是「重寫馬華文學史」的工程,他們企圖以在台馬來西亞離散華人的觀點,將在台馬華文學重新「寫回」馬華文學史的脈絡。
從馬華文學在台灣活動的第一、二種模式看來,這兩批作家的努力主要在於自我實現,或貫徹一己的「中國認同」,建構文學想像中的「文化中國」。兩者與台灣文學的系統關係其實相當曖昧,既被認可又遭排斥。第三種模式的在台馬華文學則在作者完成自己的精神或文學成長之後,以他們屢奪文學大獎的優異表現,提高了留台/旅台馬華文學的能見度。第四種模式的留台生馬來西亞本土意識相當濃烈,相對的,他們在台灣文學複系統中也處於最邊緣位置。
話說回來,即使是第三種在台馬華文學模式,其在台灣文學複系統中的位置,也屬於邊緣的模糊地帶:既在系統之內,又在系統之外。或如黃錦樹所說的:「不論寫甚麼或怎麼寫,不論在台在馬,反正都是外人」(黃錦樹 1997:4)。這種認同與被認同與認可的承認政治與焦慮,正是離散馬華文學的尷尬處境與局限,不論是在台在馬。換句話說,「在台馬華文學」或「馬華文學在台灣」更有可能是一種吊詭的現象,既為「在台馬華文學」,故依然是「馬華文學」。「馬華文學在台灣」,故不在馬,結果「在台」「馬華文學」 非但「不在」馬華文學裡,甚至也「不在」台灣文學之內。因此,它既是馬華文學史的一個缺口,又從台灣文學中間(自我)內爆。
將台灣視為「旅台馬華文學特區」(黃錦樹1990)或「馬華文學境外營運中心」,乃我們試圖解釋馬華文學在台灣文學複系統中的位置的一種方式。作為在台馬華文學的活動場域,台灣文學是否具有足夠的包容力,或台灣的本土文化論述是否朝多元主義方向趨近,或許可以從台灣文學(史)如何容納與描述這一支「外來寫作兵團」看出端倪。到底張貴興、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算是馬華作家還是台灣作家?究竟入選「中文小說一百強」的《吉陵春秋》是台灣文學還是馬華文學? 其實是文學身分屬性的問題。不過, 在台灣,在一般台灣讀者眼中,誠如陳大為所指出,「『馬華旅台文學』幾乎同等於『馬華文學』」(2001:33),儘管在馬來西亞國內還有一個「馬華本地作家」社群,而且還是以當道、主流馬華文學自居的馬華文學。
余光中在替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寫序時說此書空間曖昧,認為「就地理、氣候、社會背景、人物對話等項而言,很難斷言這小鎮是在江南或是華北」(余光中 1996:311)。不過,鍾玲到砂拉越的古晉去,看到了李永平的萬福巷。後來寫《海東青》的時候,李永平聲明他寫的是「台北的一則寓言」。到了他近期的《大河盡頭》,其實寫的已是他自己的一則寓言了。張貴興《伏虎》的短篇中多類似鄉野傳奇,空間處理也頗曖昧其詞,到了他寫《柯珊的兒女》中的〈柯珊的兒女〉與〈圍城の進出〉時,台北已成了他觀望的世界。不過,由《頑皮家族》拉開序幕,他「退回」故鄉,婆羅洲雨林成了《群象》、《猴杯》與《我思念中的長眠的南國公主》的主要場景。葉石濤在評這本小說集時坦言:「張貴興除了提供動人故事之外,我們不清楚,他究竟要闡明甚麼,到底要帶給我們怎樣的訊息?……這本短篇小說集的其餘小說……也同樣具有卓越的文字技巧,卻令人發生小說到底要求甚麼的疑問」(葉石濤1989:94)。黃錦樹在他的早期兩本小說集對家鄉的雨季與膠園著墨頗多。膠、錫與棕櫚原是馬來西亞三種主要天然資源,也是馬華文學的寫實符號。但是在黃錦樹筆下,膠園卻是恐懼、夢饜、挖掘心靈深層或政治黑區的源頭。陳建忠曾說:「這類雨林書寫其生活原非台灣讀者所能想像,而我們的馬華作家卻執意要在台灣寫其熱帶雨林經驗」(2001),認為這些作家是「失鄉的歸鄉人 」。葉石濤與陳建忠的評語代表了台灣文學對在台馬華文學的一種看法。
在台馬華作家的來台原始目的大多數是升學,正式身分是「僑生」或「外僑」。這也是黃錦樹說的:「台灣生產線」基本上是留學生現象的衍生物、副產品,因此它的主體有一部分是留學生」(2009)。這些在台馬華作家中,有些人,如陳慧樺、李永平、張貴興、辛金順,在台灣延續未留台前的作家身分; 有些人, 如陳大為、鍾怡雯、黃錦樹,來台之後方才成為作家。一般僑生來台升學居留時間其實有限,最多四五年。但是目前在台的這批馬華作家已非一般僑生,他們多半已在台居留至少十年,要不然就是已經入籍台灣,成為新移民(故要將他們的在台馬華文學視為「移民文學」也無不可),他們在台灣的職業多半是教書。不管自覺或不自覺,他們以新興或離散華文文學作家的業餘身分,在台北與吉隆坡(或古晉)之間往返,在台北與台北以外的鄉鎮(花蓮、淡水、嘉義或埔里)之間穿梭。晚近新興英文文學作家,如奈波爾(V.S. Naipaul, 1932--)、魯西迪(Salman Rushdie, 1947--)、穆可芝(Bharati Mukherjee, 1940--)等人往往游離原籍國,長年移居歐美國際都會,可能是自我放逐,卻不一定是文化回歸。這些在台馬華作家也未嘗不是如此。因此我以新興英文文學對應馬華文學,視馬華文學為「流動的華文文學」、「跨國華文文學」及「新興華文文學」的例子。
「旅台馬華文學特區」與「馬華文學境外營運中心」的說法,其實也頗能彰顯在台馬華文學在馬華文學複系統中的位置。對在馬來西亞的馬華文壇而言,這支在台灣的馬華文學隊伍的文學表現可能是無根的、遠離本土的、非寫實主義的、甚至台灣化的。在台馬華作家的書寫風格技巧,細究起來,跟在馬來西亞本土的華文文學可能也有細緻微差,但是那種文體上的差異來自文學視野(寫甚麼,該怎麼寫,乃作家一輩子的重要思考課題),非關地理眼界。其實,早在一九七二年至七四年間,在台灣的《中國時報》與馬來西亞的《蕉風月刊》,馬華作者的離散與歸返現象,已引起多方論辯。當年論戰所針對的其中一種說法是,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主流,故星座詩社諸人留台,即從馬華文學自我放逐而回歸主流。本土馬華主體意識強者對此說則頗有微辭。不過,從今天「在馬與在台成了馬華文學的兩條生產線(雙軌)」(黃錦樹2009)的觀點來看,反正在台在馬生產的都是馬華文學,作者歸返哪個主流,就沒那麼重要了。
八、九○年代以來,這個寄生在台灣的馬華文學風潮由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黎紫書的小說,林幸謙與陳大為的詩,林幸謙與鍾怡雯的散文所形成。而且台北幾家主要的文學書籍出版社都出版過馬華文學,成為馬華文學台灣生產線的贊助者。平心而論,以離散馬華文學這樣一個小規模的文壇來說,在同一個時期,有七位創作力旺盛的作家在國內國外共同努力實踐,已足以形成一股潮流。正是這股潮流凸顯了馬華文學在一九九○年代興旺蓬勃發展,並以新興華文文學的面貌展顏,同時馬華文學論述也躋身國內外學院裡的學術研究領域的現象。因此說馬華文學也受惠於這批留台作家並不為過。
即使是發生在馬來西亞本土的馬華文學,多年來也有不少留學台灣的作家在努力打拼,例如陳強華與傅承得,他們多半在留台期間完成作家的「成長儀式」,然後返回故鄉,或教書、或在報館服務、或開書店、或辦出版社,為馬華文學發展做出貢獻。同樣的,商晚筠在一九七七年獲得聯合報文學獎,在台灣出版了第一本短篇集《癡女阿蓮》,儘管她回馬之後的發展並不理想,到了一九九一年才在台灣出版第二本小說集,卻是八○年代馬華文壇重要的女作家。而潘雨桐在六○年代初即留學台灣,八○年代由聯合文學出版了兩本書後,在台灣書肆行情漸漸消失,但是他持續在馬來西亞發表作品,是頗受重視的馬華小說家 。
本節徵引書目
陳大為(2001)〈躍入隱喻的雨林:導讀當馬華文學〉。《誠品好讀》13:32-34。
陳建忠(2001)〈失鄉的歸鄉人:評黃錦樹編《一水天涯:馬華當代小說選》兼及其他〉。《四方書網》http://www.4book. com.tw。
陳鵬翔(1992)〈校園文學、小刊物、文壇:以《星座》和《大地》為例〉。 陳鵬翔與張靜二(編)《從影響研究到中國文學:施友忠教授九十壽慶論文集》。台北:書林書店。65-82。
陳鵬翔(2001)〈歸返抑或離散:留台現代詩人的認同與主體性〉。林明德(編)《台灣現代詩經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99-128。
黃錦樹(1990) 〈「旅台文學特區」的意義探究〉。《大馬青年》8:39-47。
黃錦樹(1997)〈非寫不可的理由〉。《烏暗暝》。台北:九歌出版社。3-14。
黃錦樹(2009)〈十年來馬華文學在台灣〉。《南洋商報.南洋文藝》1 Sept.:14-15。
溫瑞安(1974) 〈江湖路遠:《將軍令》跋〉。《蕉風月刊》259:42-44。
夏志清(1979) [1975]〈余光中:懷鄉與鄉愁的延續〉。周兆祥(譯)。黃維樑(編)《火浴的鳯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台北:純文學出版社。383-90。
葉石濤(1989)〈評張貴興《柯珊的兒女》〉。《文訊雜誌》ns l:92-94。
余光中(1996) [1986]〈十二瓣的觀音蓮:序李永平的《吉陵春秋》〉。《井然有序:余光中序文集》。台北:九歌出版社。311-19。
鍾玲(2000)[1993]〈我去過李永平的吉陵〉。《日月同行》。台北:九歌出版社。19-29。
本文出自:張錦忠《馬華文學》,西灣文庫。
[1]陳鵬翔(陳慧樺)說他們原本要辦的是一本叫《中國文學》的綜合性文學雜誌,見陳鵬翔 199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