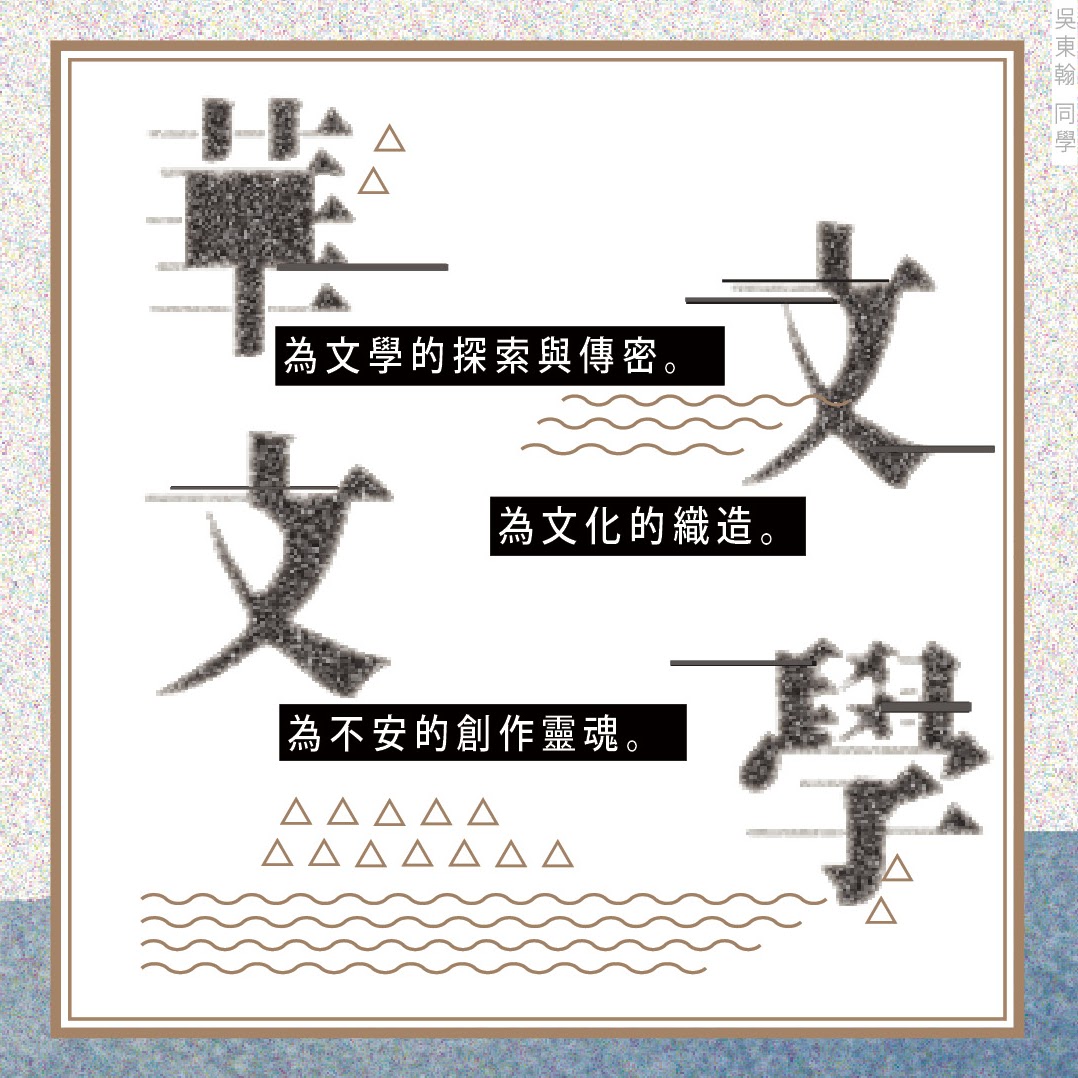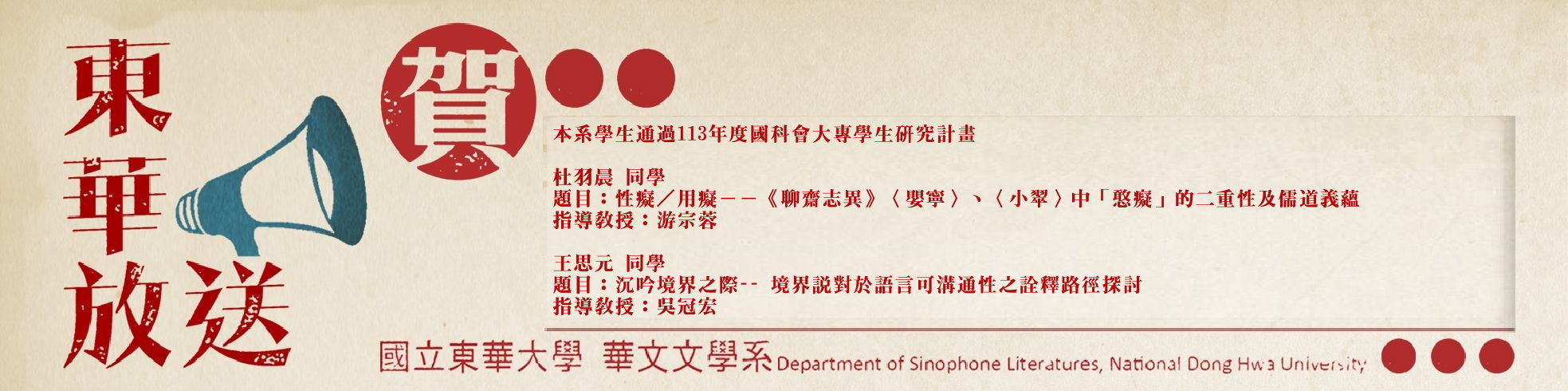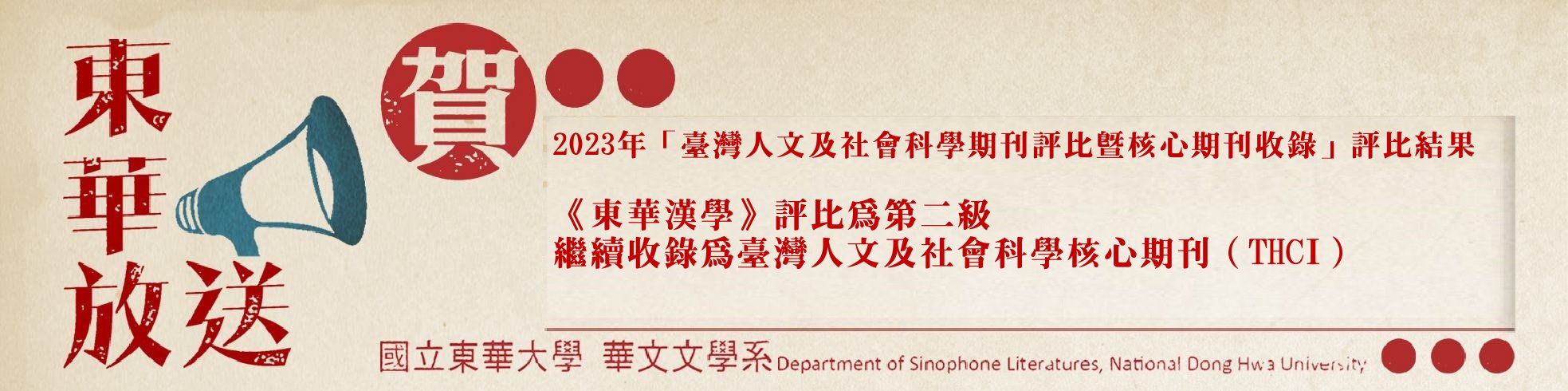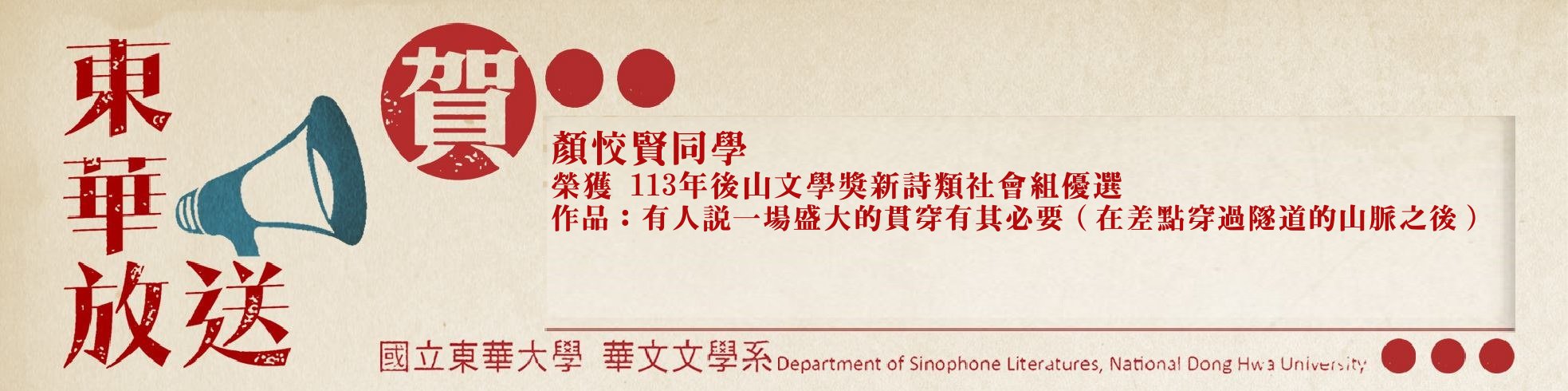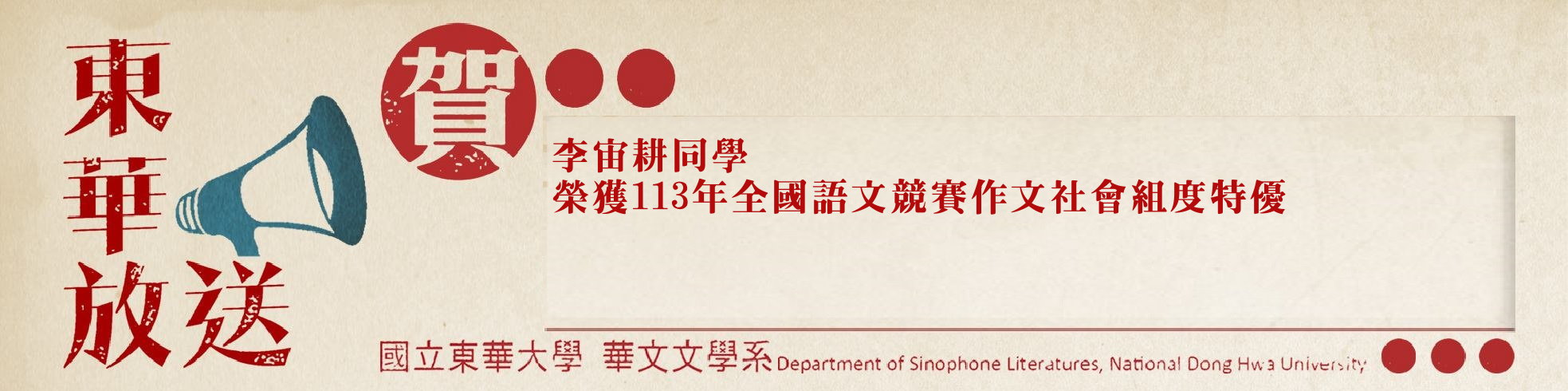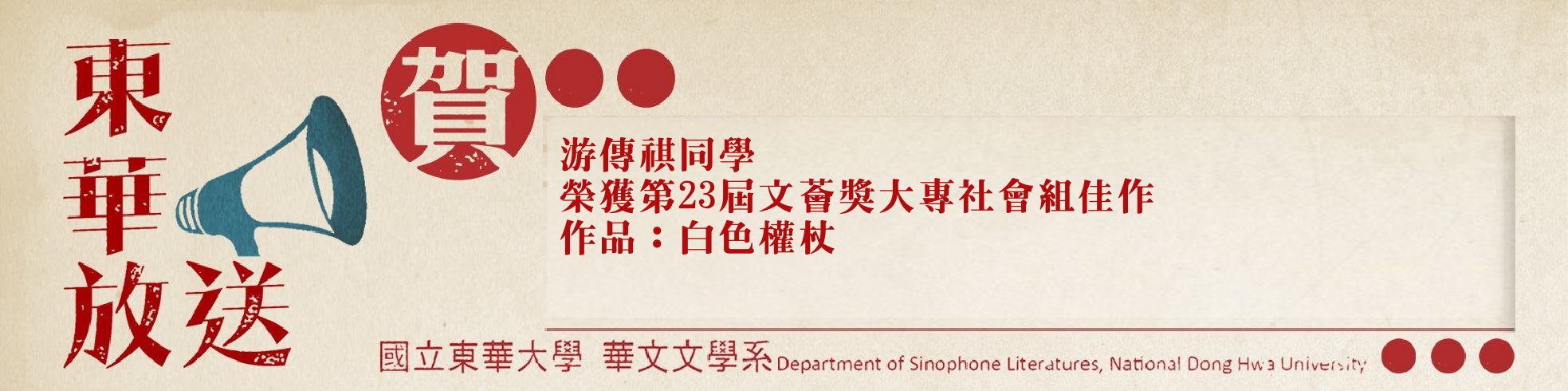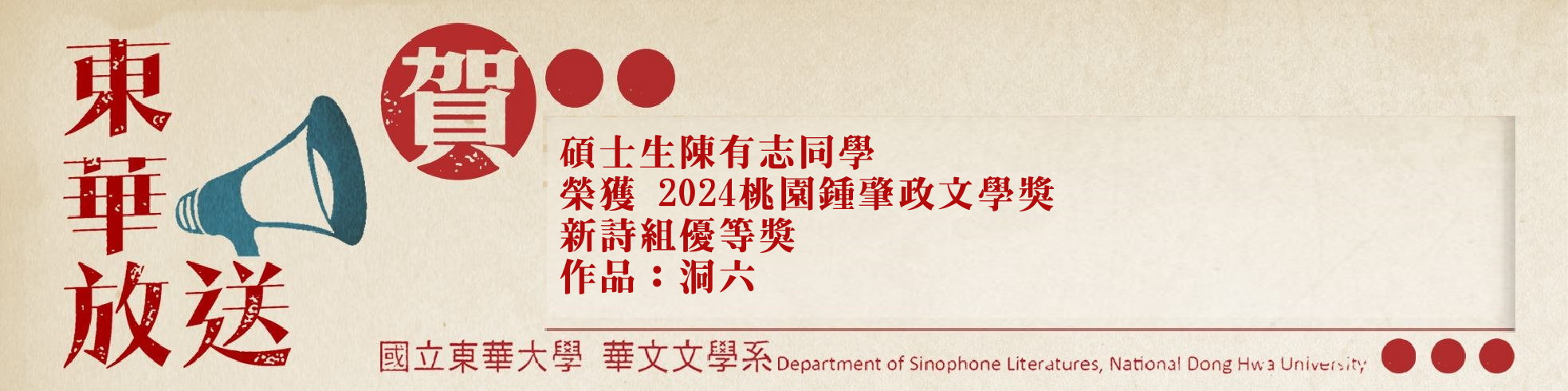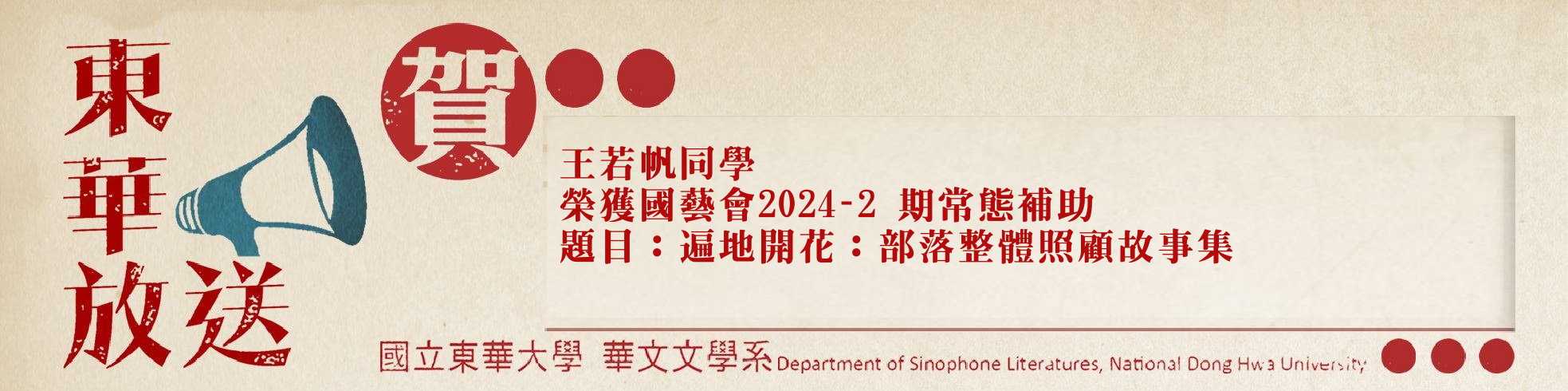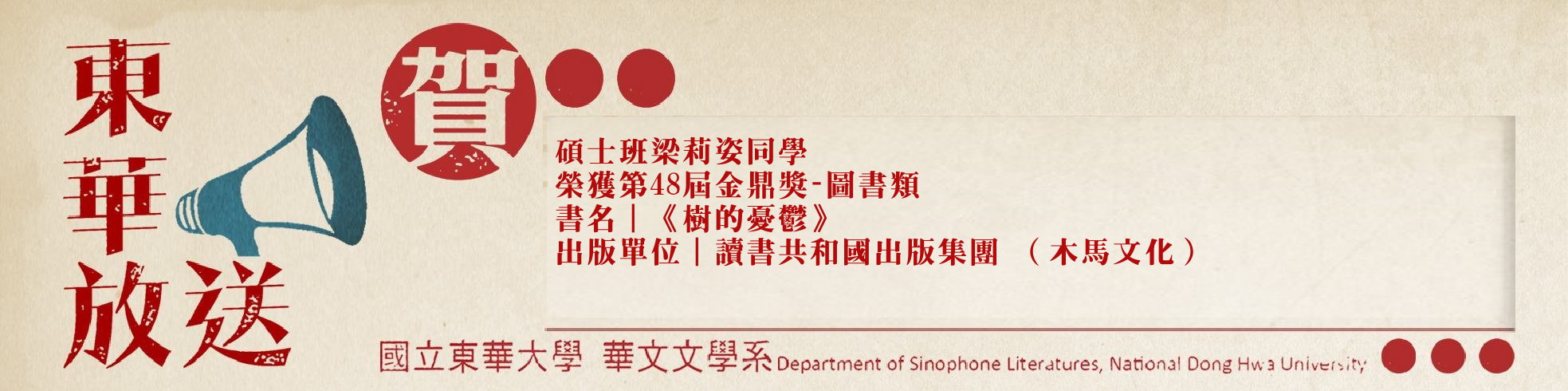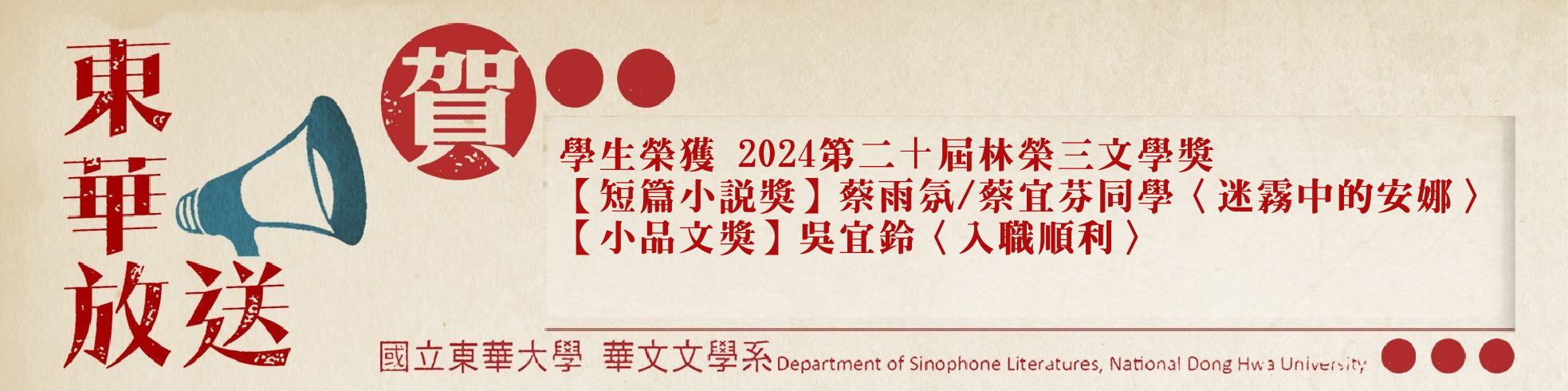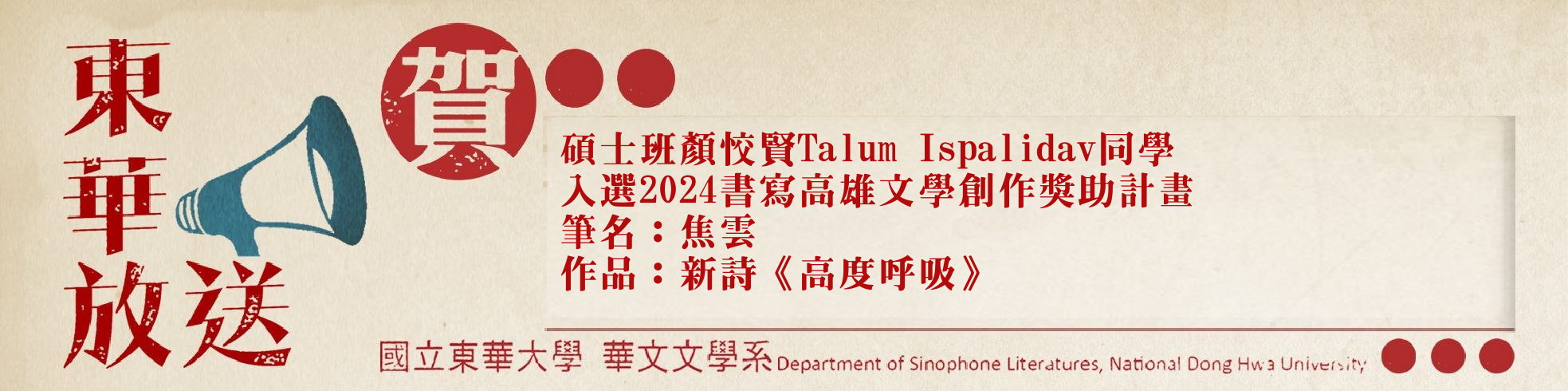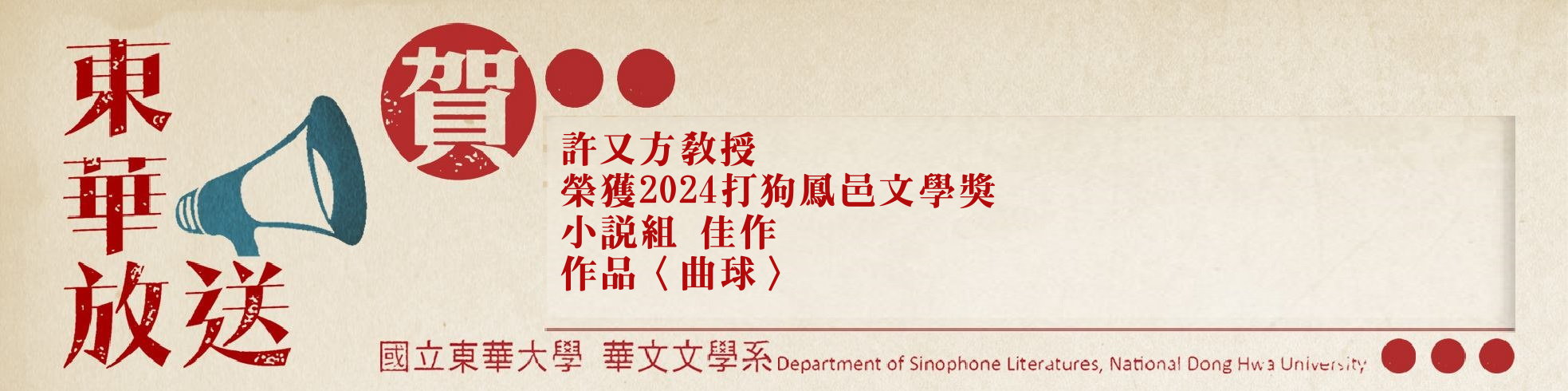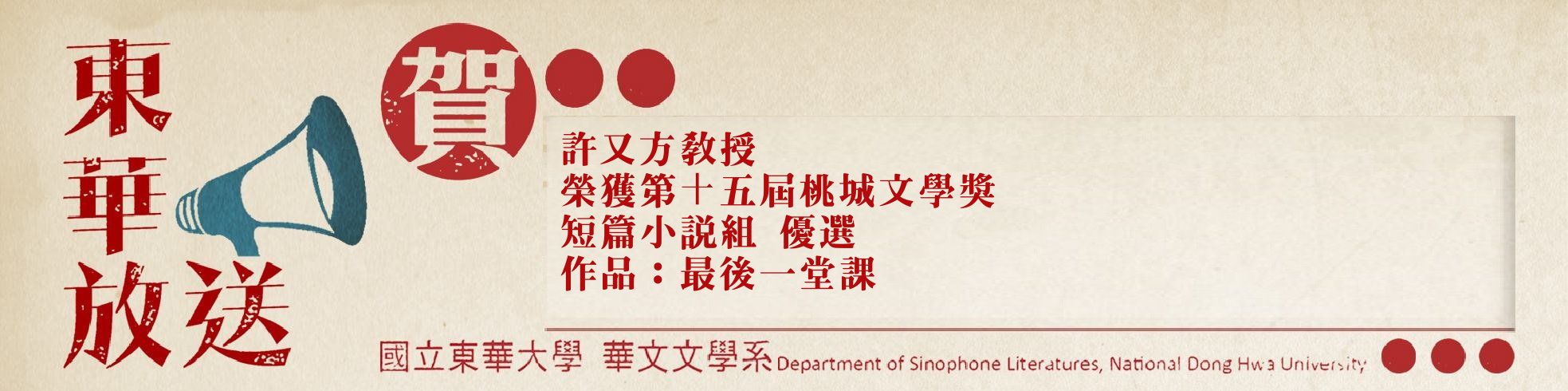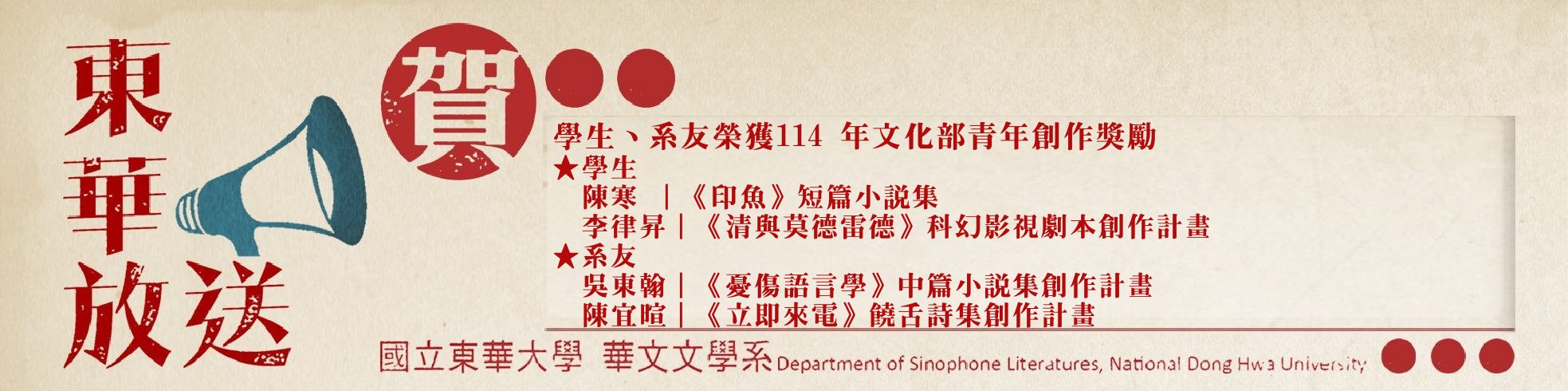【關於馬華文學】〈馬華文學的定義與屬性〉《馬華文學》∣ 張錦忠
馬華文學的定義與屬性
張錦忠《馬華文學》
「馬華文學」一詞,泛指馬來亞(含新加坡)或馬來西亞(含婆羅州的沙巴、砂拉越及一九六五年前後的新加坡)的華文文學作品,尤其是指一九二○年代以降在這個東南亞地區發生的白話華文文學。換句話說,馬華文學(或馬華文藝)即(廣義的)華裔馬來西亞人用華文書寫或在馬來西亞境內或境外以華文書寫的文學作品。這樣的界定顯然定向於語言媒介或語系。不過,在一般情況的定義下,由於缺乏語意的限定條件,「馬華文學」一詞也可能指涉另一個稱謂── 馬來西亞華人文學。這就將馬華文學歸類於族裔文學的範疇了。
為了更清楚區隔「馬華文學」作為族裔文學與語系文學的指涉邊界,另一個詞彙乃因應而生──「華馬文學」,作為「華裔馬來西亞文學」的簡稱。另一方面,使用「華馬文學」一詞,也表示純粹從語文的角度來界定馬華文學、並無法彰顯其複系統性質,因為它相當一廂情願地假設馬華文學的書寫者是華人、淡米爾文學的書寫者是印度裔、[1]馬來文學的書寫者是馬來人、只有馬英文學的書寫者才可能包括各種族作家。此外,華人社群所產生的文學作品,也並非只有以白話中文書寫。
早在十九世紀,就有土生華人(或稱峇峇[Baba]、海峽華人)以峇峇馬來文及英文創作及翻譯。同樣在十九世紀,在中國駐新加坡各任領事的提倡之下、再華化運動興起,新馬古典詩文活動盛行一時。二十世紀中葉,本地創作英文文學興起,馬英詩人中尤多受英語教育的華裔。獨立以來,馬來文成為國語,在非馬來人間日漸普及,更不乏以馬來文創作的華人作家(例如林天英),因此,我們應該視「華馬文學」為一包含華裔馬來西亞人創作的白話中文文學、古典中文文學,峇峇馬來文學、英文文學、馬來文學、以及淡米爾文學或其他語種文學的文學複系統。 這個詞彙的上述指涉已見諸例如《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張錦忠、黃錦樹與莊華興合編)的書名脈絡。
不過,在歷史、社會、文學進展的過程中,華馬文學複系統中的若干系統或次系統之命運也不盡相同。峇峇馬來文學早已終止運動,成為歷史現象,如今沒有人以「峇峇馬來文學」指稱當代華裔作者以標準馬來文書寫的產品(例如林天英的詩作)。古典文學則在二、三○年代白話文學興起後漸漸退居邊陲,儘管到今天還有馬華古典詩人結社吟詩或印刻舊體詩集,而且其中不乏名家。此外,由於英文教育在七○年代以後日趨沒落,馬華英文文學始終在主流之外,若干知名詩人,如余長豐(Ee Tiang Hong, 1933-1990),陳文平(Chin Woon Ping)、林玉玲(Shinley Geok-lin Lim, 1944--)早已移居他鄉,小說家李國良(Lee Kok Liang, 1927-1992)也已辭世。如今在華馬與馬華文學各種論述與建置空間當道的,是以白話文為主的現代華文文學。因此,在許多馬華文學論述裡,「馬華文學」,指的就是白話文學。
作為族裔文學,「馬華文學」為離散華人(離開中國散居他鄉的華人及其後裔)的華文書寫。離散中國人在移居地取得身分證,成為公民或居留者,結束其離散或移徙行為,有了「從屬國家」,而其後代則在移居地土生土長,成為移居地的「族裔」。但是,這個移居地的離散中國人族裔,在名義與本質上難以擺脫其離散歷史或離散族裔性,這也是離散華人在馬來西亞歷史上有別於其他族群的差異來源。故馬來西亞華裔仍然屬於「離散華人」,其文學書寫也具有這種離散文學屬性。
不管是作為族裔文學還是語系文學,「馬華文學」一詞其實充滿了政治身分與文化認同的重重問題。其文本性不是在小我或私人空間建構,而是在社會經濟政治的公共空間構成。這個用語一方面表示,在馬來(西)亞這個地理空間,一個包含馬來文學、馬華文學、馬印文學、與馬英文學的(多語)馬來西亞文學複系統的存在。但是,由於馬來人主導的政府在各個公共領域皆實行「卜米主義」(Bumiputraism,即馬來人與馬來文化至上論),長期以來這種意識形態壟斷國家機器,在官方論述與文化計畫機構(如教育部、語文出版局)的認可政治議程中,只有馬來文學才具備國家文學的資格,其他語系文學則被從屬國家屬性分割出來,只能屬於區域文學(sectional literature)。這個區域文學的存在與活動空間局限於邊陲地帶,在官方公共論述中毫無能見度可言。
另一方面,相對於強勢的中國文學,離散馬華文學,以及其他華語語系文學,乃屬一支弱勢「小文學」(literature mineure / minor literature)。「小文學」為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1925-1995)與瓜達里 (Felix Guattari, 1930-1992)一九七五年論述卡夫卡及其書寫時提出來的理論。將德勒茲與瓜達里二氏的理論譯為「小文學」,難免令人望文生義,以為是一國之內的少數民族語言的文學,或如華文之相對於馬來文為國境內的弱勢語文,故華文文學位居邊陲,其實不然。小文學之成其小,在於其乃在主要語文內所建構而成。以馬華文學而言,乃東南亞「華文」之對於中港臺的「中文」。從中國或港臺離境的「中文」,到了南洋,處身多語的南方,成為去畛域化的「華文」,這樣的「破」華文,其特色為詞彙貧乏、修辭淺顯、句法怪異、甚至充滿「異國情調」,簡直是歧文異字。馬華作家即用這樣去畛域化的「東南亞華文」創作。
依據德、瓜二氏的說法,小文學或「南洋華文」有下列三特質:(一)去畛域化;(二)政治性;(三)集體價值。身為布拉格的猶太人,卡夫卡以德文書寫,依小文學理論,乃「不可能」的現象── 不寫之不可能,因為民族意識的存在必須藉由文學彰顯;不得不以德文創作── 因為捷克原鄉畛域已不在;但是以德文寫作也不可能── 因為這樣的德語已去畛域化,為與群眾隔離的少數民族用語。因此,「簡而言之,布拉格德語乃去畛域化的語文,用法怪異,用途卑小」(Deleuze and Guattari 1986:17)。其次,小文學的特質是這些文本充滿政治性。大文學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作家個人關注,小文學的壓縮空間則將小我放大成大我:伊底帕斯三角習題被淨化成社會政治經濟議體。第三,由於具個人才氣的大家並非小文學的普遍現象,個人的發聲無法和集體聲音分開。「其實,具才華的大作家不多反而是好事,這樣一來非大家文學才得以出頭;每一位個別作者的看法也就略同人人所見」,文學也因此得負起「集體發聲── 甚至改革── 的功能與角色」(Deleuze and Guattari 1986:17)。
作為小文學,馬華文學的意義與價值,不在於誰是大作家,或個別優秀作家產生了多少經典,而在於其集體性。在這樣的集體性認同脈絡下,作家所創作的是一種非大家、無經典的「小文學」,代表集體發聲。首先,馬華文學作者的去畛域化(從華文進入中文),已是某種集體性的認同,例如李永平從《拉子婦》進入《吉陵春秋》。換句話說,在沒有大師或大作家有如鳯毛麟角的階段,「經典缺席」也不是壞事;甚至正好相反,「經典缺席」彰顯了這種集體性──集體認同或認同集體(「馬華文學」),而非大作家 。
小文學作品展現了語言與想像的去畛域化,從「中文大國」觀點來看,簡直充滿異國情調,或上文所說的「歧文異字」,其實也是多語主義轉向。從這個角度來看,在作為「小文學」產品的《吉陵春秋》中,李永平刻意錘鍊的純正書面語文,可視為試圖操作去畛域化及再畛域化的案例。再畛域化指小說建構了李永平自己所說的對「中國文字的純潔與尊嚴」的追求。但是這種追求何嘗不是同時對身處語境與歷史文化的批判,因為「中文大國」的重要語言的理想竟由小文學去實現。
簡而言之,當我們使用「馬華文學」一詞時,它總已涵蓋離散、族裔、語系、小勢、去畛域化、再畛域化、邊陲的指涉性。
本節徵引書目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1986) [1975]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本文出自:張錦忠《馬華文學》,西灣文庫。
[1] 淡米爾語(Tamil)屬於達羅毗荼語系,為印度南部、斯里蘭卡東北部,及東南亞印度裔社群通用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