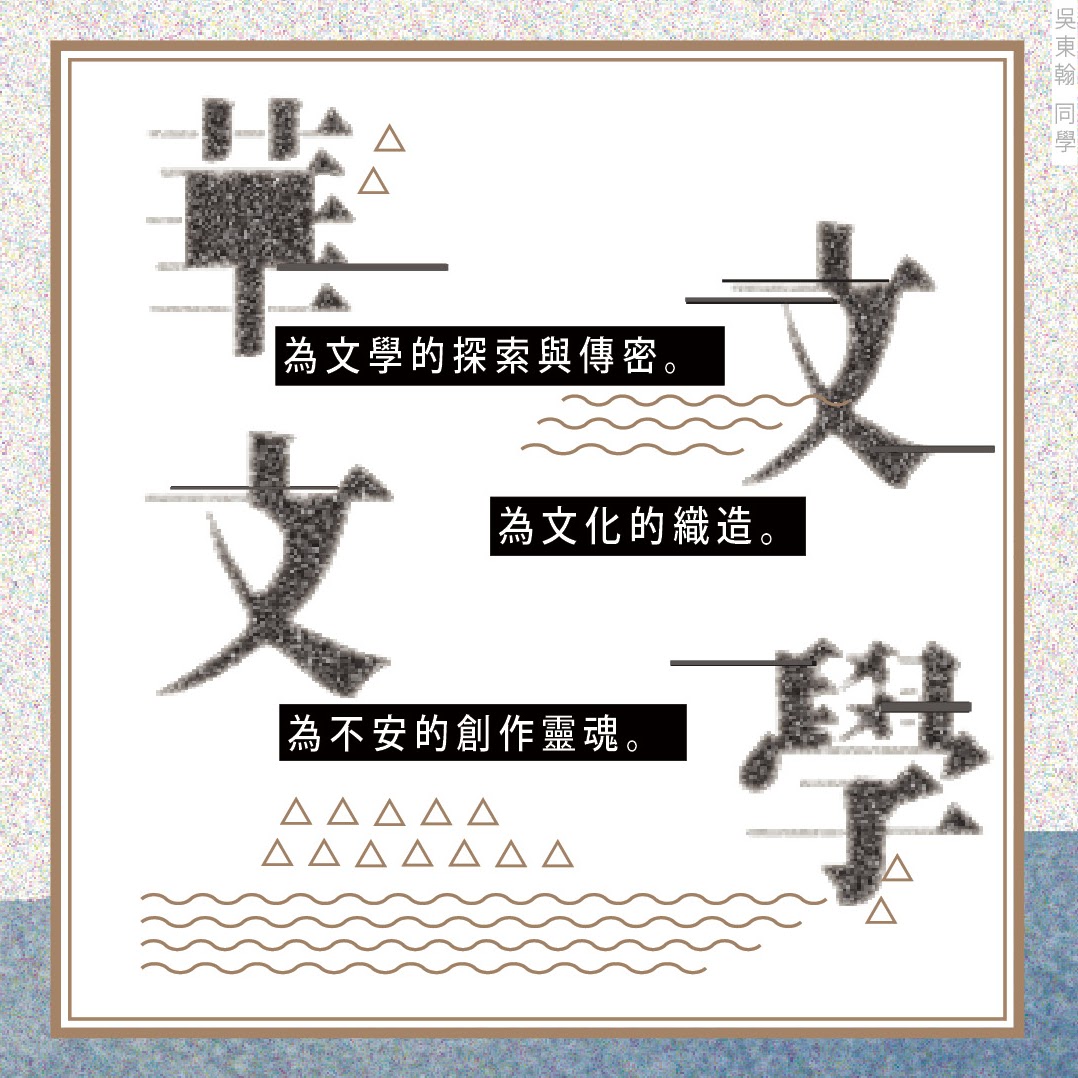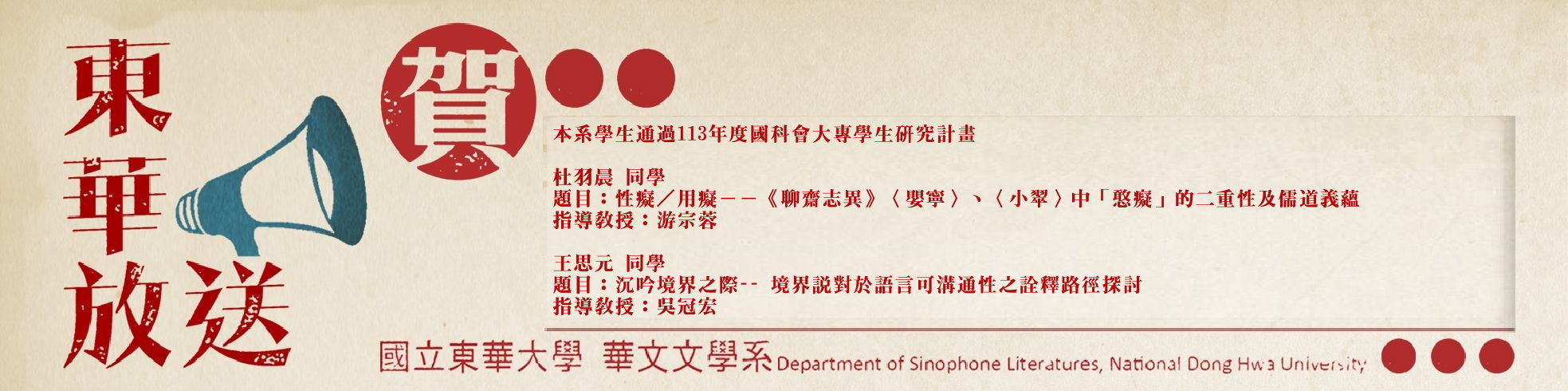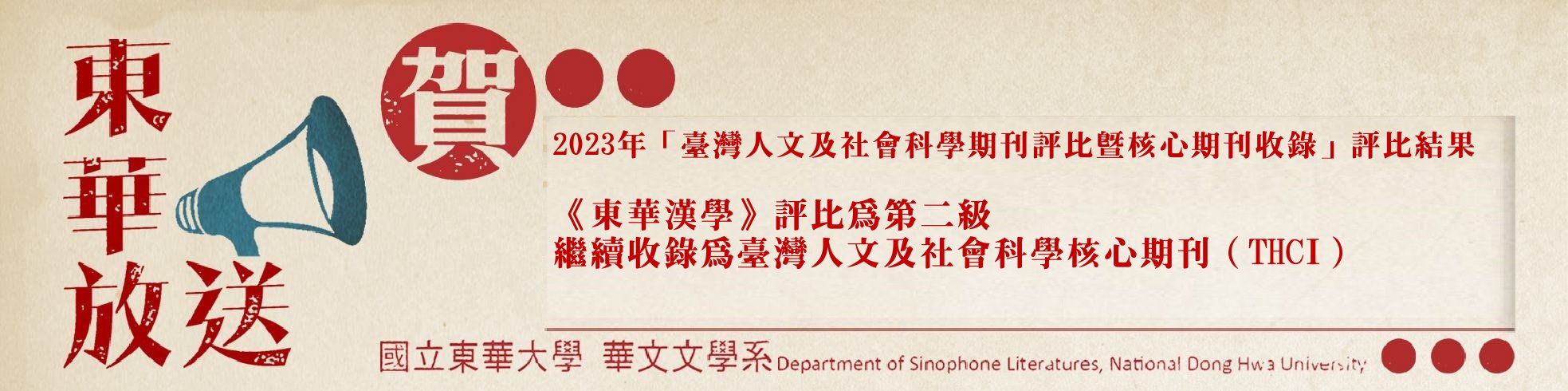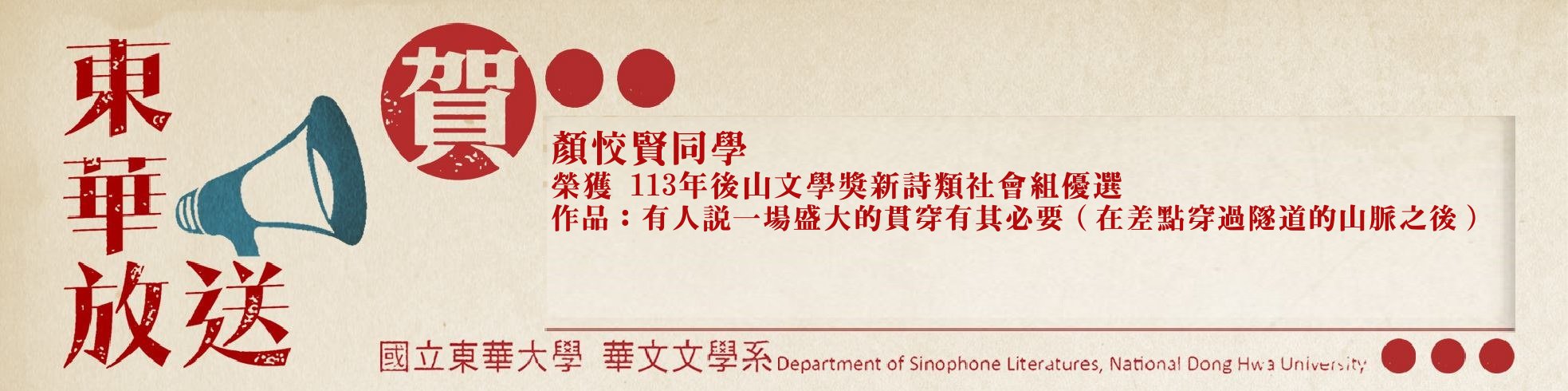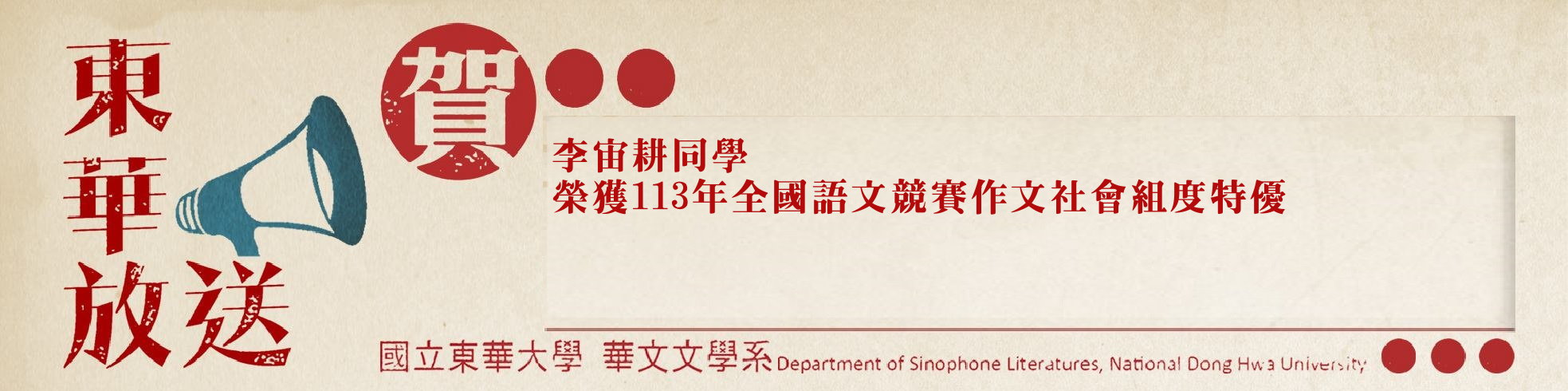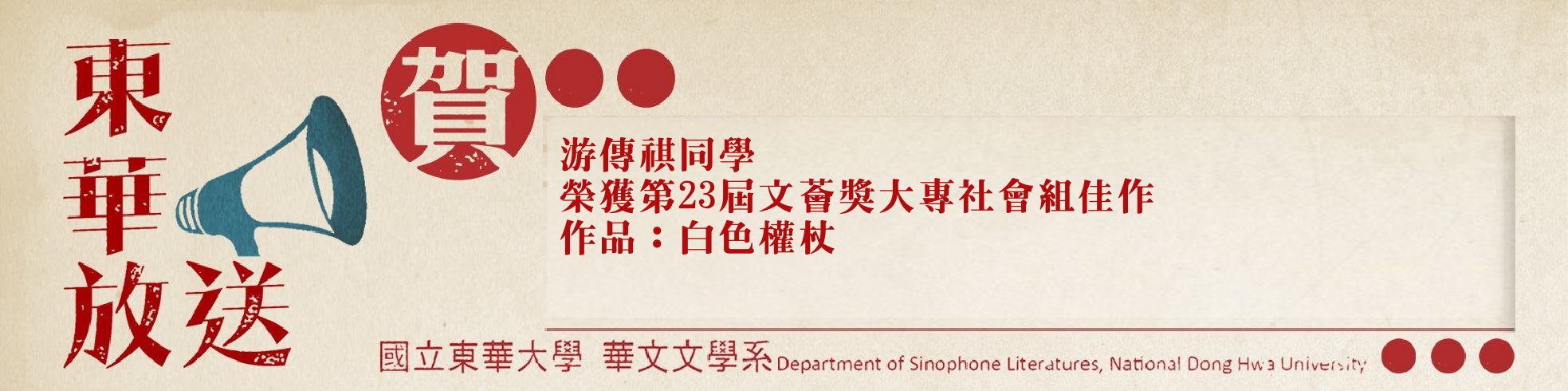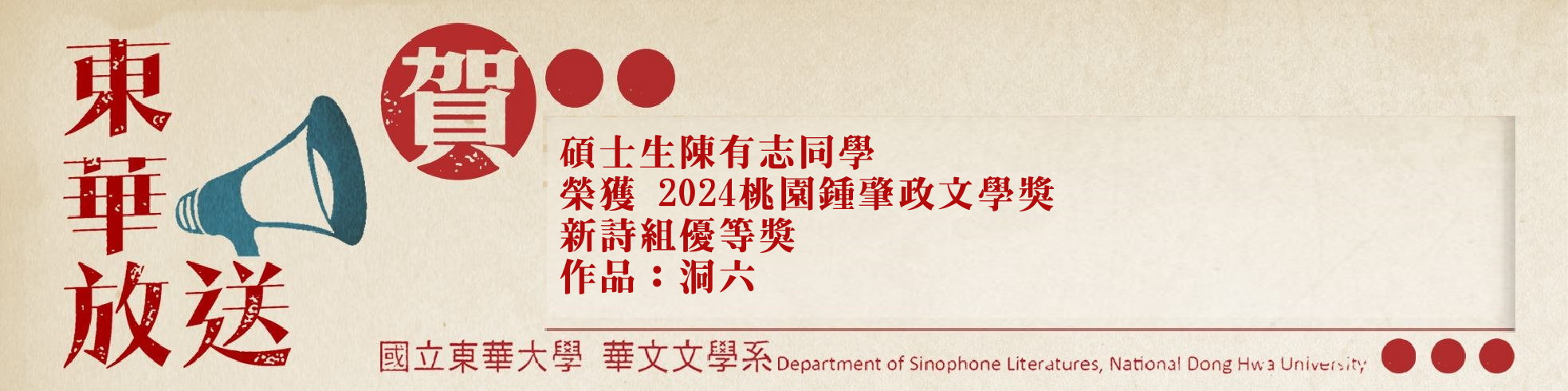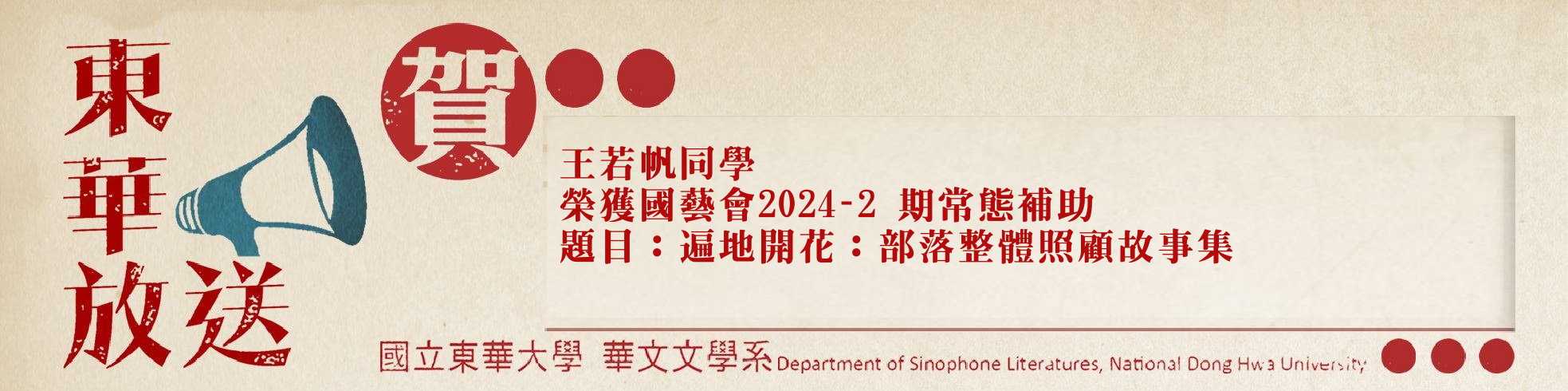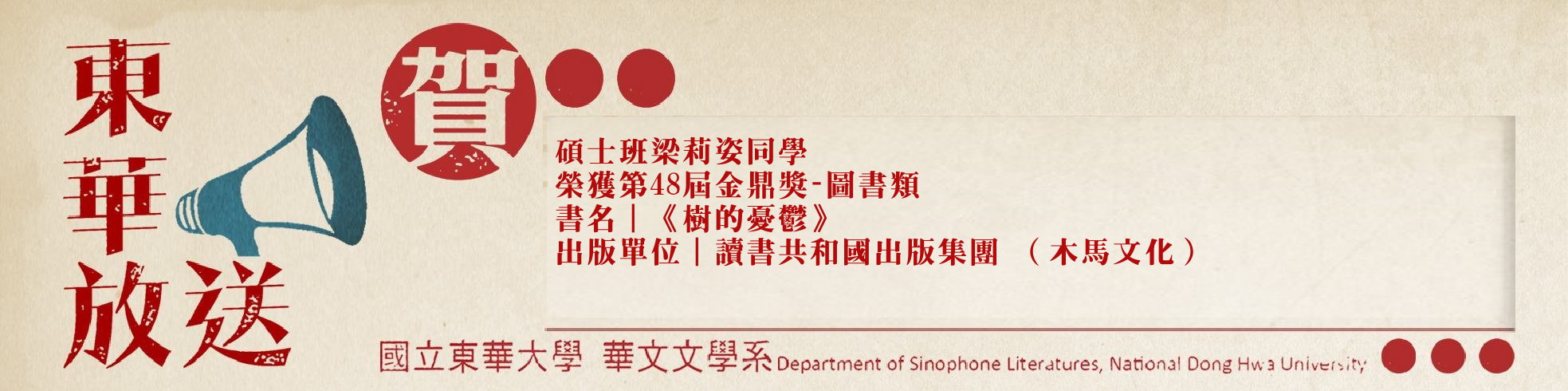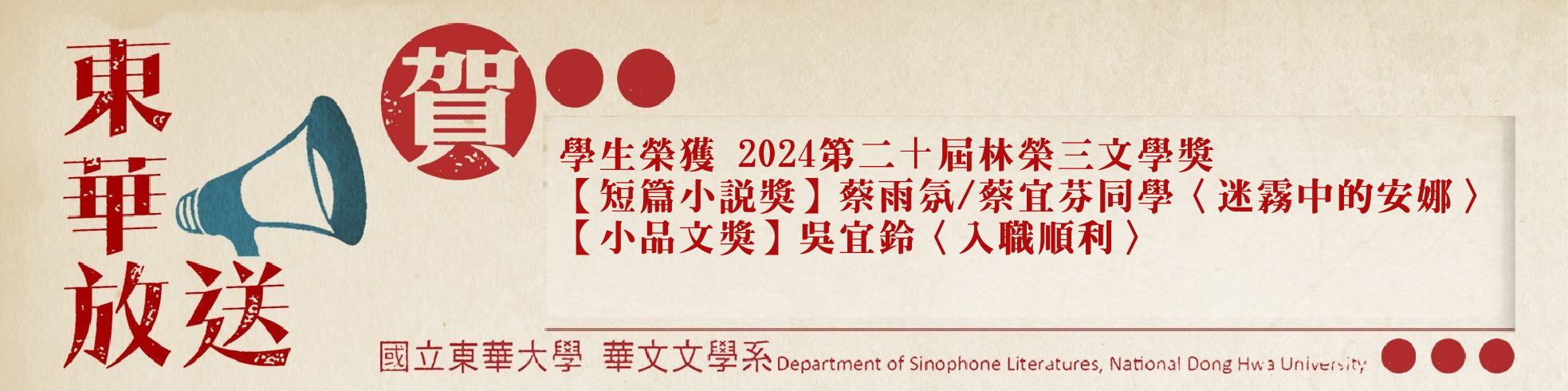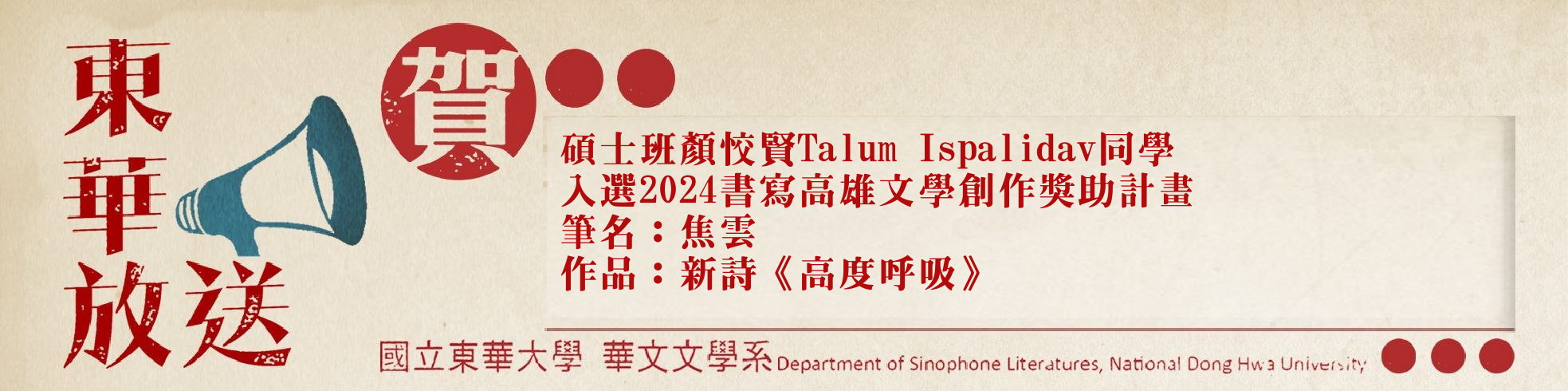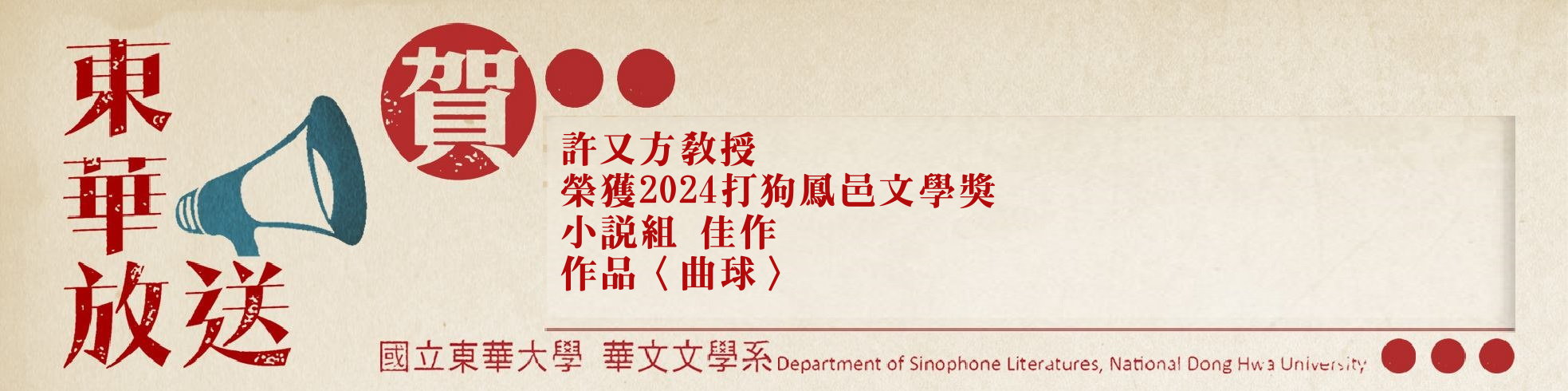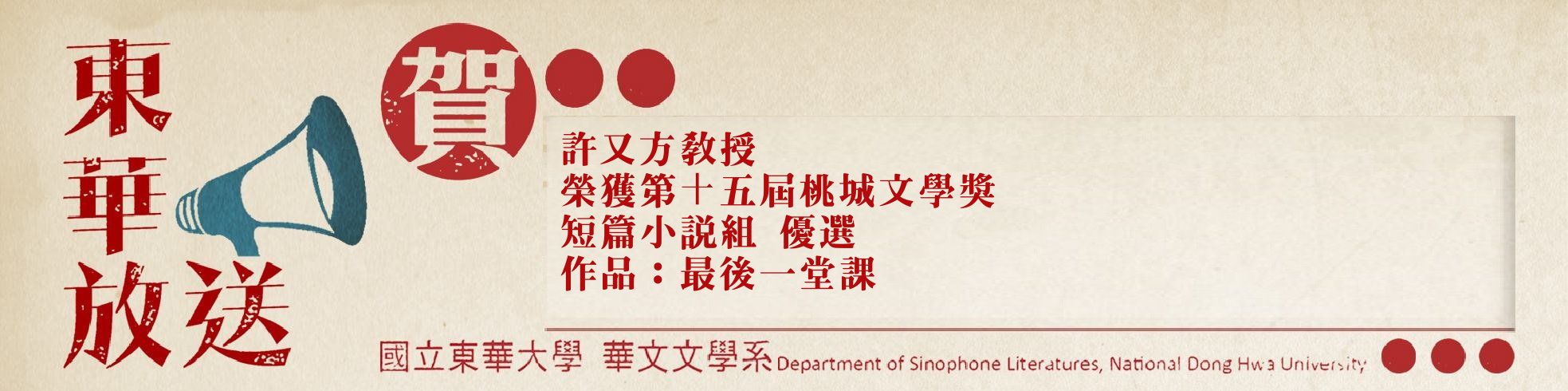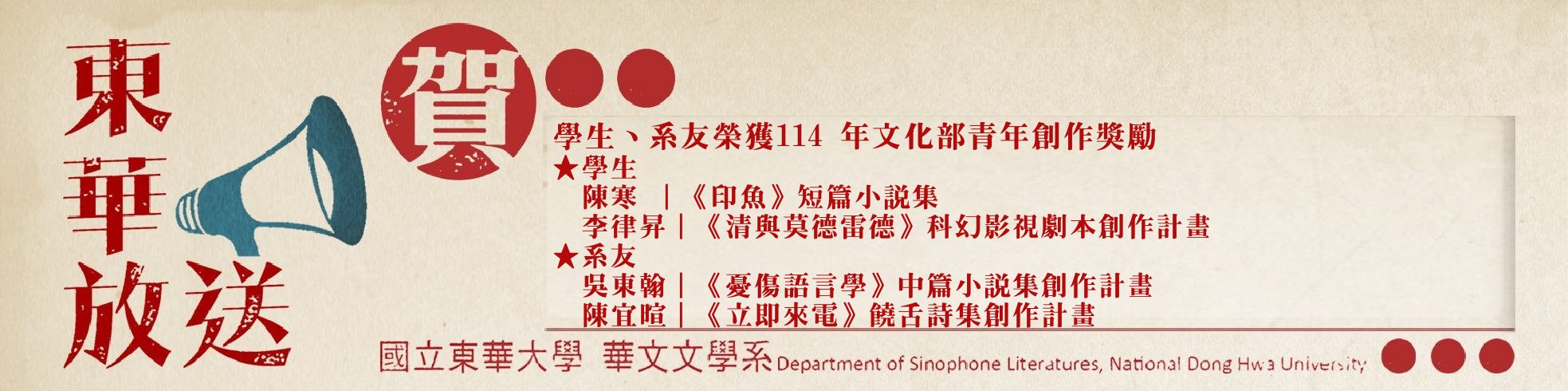演講紀錄【王和平老師】| 放一支麥克風在腦中:詩的發聲可能
主講人∣ 王和平老師
講題∣ 放一支麥克風在腦中:詩的發聲可能
主持人∣ 張寶云老師
日期∣ 2025.12.05
地點∣ 人一第三講堂(C109)
【演講紀錄∣劉柏萩】
王和平小時候玩過一種玩具,只有兩個按鍵say和play,大概可錄製六秒的聲音,長大後,變成一顆紅色錄音按鈕,她說,錄音是一種魔法,當我們在聽自己錄下的聲音,是會存在於當下,不是過去或未來。
在工作一段時間後,參加內觀營,一進入就先收手機,也不可以書寫和閱讀,與人交流也不被允許,在這樣的場所,感官會全部打開,你會看見世界的擾動,靜坐、散步,一段經文她反覆念誦,「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而且是用廣東話,她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母語是這麼美,句子的意義是什麼,她不管,聲音才是感受的主體。
《過動公寓》作為一本詩集出版,講者把自己關起來兩次,她想要把詩集錄下來,借用朋友的工作室,不斷的嘗試,用自己會的語言錄製,像是回到小時候玩玩具的樣子,裝備升級,本質上是相同的。
王和平在唸音樂所讀到「樂動」,社會音樂學家Christopher Small於1998提出,他把 Music (名詞) → Musicking (動詞),把音樂變成一種帶有社會性與互動性的關係,音樂給觀眾的感覺,播放黑膠的唱片震動,「樂譜是死的,音樂是活的」,作品的當下已被完成,但是經過傳播解讀,音樂正在流動,於是講者開始思考,那文學呢?文學可以樂動嗎?如果文學也可以動,那過動公寓怎麼動?
她首先設計了海報,規劃幾場演出,為這個未完成的作品做了一場實驗,在得到觀眾反饋後修改,也逼自己去完成它,她總覺得她開了空頭支票,因為她的作品還沒完成,卻又要表演給大家看。
《怪咖啡因》的製作不像傳統專輯的出產,她是在不斷的嘗試與失敗之中,得到一個實驗性的詩專輯,而這正是藝術的本質,創造,本來就是無止盡的嘗試,似乎想要突破某種框架,從本來想要to home回歸自身,轉向為聲音的純粹,作為不懂語言的聽者,我們透過聲音的表演,來轉譯為我們了解的,成為音樂。
【演講紀錄∣賈美玲】
一. 開場:
我的角色或是我的任務是一個講師 ,但是回到我自己的日常, 其實我就是一個不停的失敗又嘗試, 又失敗又嘗試的一個創作者而已。今天這個機會想要分享我自己最新作品裡面的一些思考、满足跟我最近可能在想什麼等等,希望也可以引發你們一些思考。
二. 講座內容:
你們一開頭聽到的那首歌叫做《敬我們的過動公寓》是我詩專輯《怪咖啡因 BLAME IT ON THE CAFFEINE》的主題曲, 也是今天的題目。 這個詩集是從我的《過動公寓 》詩集中摘取了15首詩分別做成曲子,再讓它去跟聲音做一個碰撞; 我好像是重新讀一遍ˎ身體再吸收一次,然後吐出一個新的東西出來。最後發表的形式就是一個卡帶。
為什麼是卡帶?
我看著它在錄音機轉的時候就覺得好像我把我所有的迂迴、 我的內向都捲在裡面; 看到捲的時候, 好像是看到一種時間的流動在裡面 。
A. 回顧之前兩堂課:
上兩堂課, 我跟大家讀了一些詩, 也分享各自的詩觀; 然後我也跟大家一起從身體出發, 比較直覺性的詩的工作坊 , 就是我放了一些節奏, 發了卡夫卡的《變形記》第一章文本給大家, 要你從一個現有的文字, 透過刪除去建構另外一種敘事的空間; 等於說你破壞了現成的文字, 然後拿回你自己的聲音和自己的敘事空間。
我們還讀了《陰道獨語》這個劇本的一些片段, 我覺得它整本書就是一首詩,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比一個生命的誕生更詭異更像詩; 就是從一個空間來到另外一個空間。「陰道」這個東西它本來明明就只是一個人體的器官, 但在我們的社會裡面卻好像是一個不能明說的禁忌, 但是它又是一個生命的出口, 所以我總覺得這好像跟詩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就帶大家讀了一些它的文字。
上一堂課, 我們做了聆聽的練習--聽雨聲。大家在那五到十分鐘嘗試去聆聽跟分辨我們很熟悉的環境之中的聲音。 在課堂快結束之前, 我們Sound Walk 聲音步行; 一群人跟著同樣的節奏, 往同一個方向走。把意識放在聽覺上 , 看可不可以開啟一些別的感官。希望之後收到你們作業的時候, 可以看到大家當時的一個心態模樣。
所以, 其實上一堂課很多的東西都是來自於這本小書, 叫做《聽見聲音的地景》, 書裡面有很多聆聽的練習, 引導你想像最遠的聲音是什麼? 最近的聲音是什麼? 重新訓練我們的耳朵。
我們後來也提到藝術史之中的一種錯置, 一個邊界的問題. 一個音樂家John Cage有一個很有名的曲子《四分三十三秒》, 他請一個鋼琴家在臺上開啟一個鋼琴就坐下來, 然後什麼都沒做, 偶爾翻琴譜的葉子, 就在那邊坐了四分鐘, 之後結束。在那個過程中, 觀眾覺得很疑惑, 你要帶給我們什麼? 他其實想要argue的就是所有聲音都可以是一種音樂, 包括觀眾的煩躁, 或是人體一種觸摸的聲音, 所有的這些雜音都可以是音樂。從此整個音樂歷史改變 了許多。
我們也講到如果一個動作可以是一個雕塑, 一句話可以是一個指令, 一個事件的樂譜, 那詩它有什麼可能性? 就是在各種錯置或是媒體的邊界模糊之中, 「詩」它有什麼可能性? 除了文學獎或是現有的框架之下, 你還可以做一些什麼? 還有什麼更好玩ˎ更直觀或是刺激的東西?
我自己的詩觀, 一直以來都是滿簡單的, 就是想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讓悶住的聲音響亮; 不想生活的太有張力, 像這個路上悶住的喇叭裝置一樣。
B. 我的創作者身分。
這是我小時候的一個玩具。它上面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say, 一個是play。 你按下say就可以大概錄下六秒鐘的聲音或是空氣; 按play的時候它就會一直重播。 我非常的著迷放在嘴邊按say,再放在耳邊按play ,不停的重複;後來我發現這個小小的玩具好像是一種錄音軟體的一個原型。長大以後我還是追隨著那個紅色的錄音的按鈕; 這個按鈕有一個魔法就是你戴耳機按下去錄音的時候, 第一個聽到的人就是你自己。對我來說最療癒的地方就是彷彿可以讓時間停止, 在按下去的瞬間突然覺得過去不存在, 未來你暫時也不會想, 完全的活在那個當下, 關注接下來要做什麼, 現在要做什麼, 這是錄音對我來說的魔法。
C. 分享2023年的內觀經驗
2023年的時候我有一個比較長的假期,在臺灣參加了一個靜修營,就是10天的內觀;內觀就是你正式入營之後,沒收你的手機,你不能跟任何人講話,你會有室友,但是他們不鼓勵跟任何人有眼神的接觸,盡量不要跟人產生什麼緣分。如果我們上一次那個Sound Walk是開啟了一個聽覺的感官,我覺得那個內觀是一件開啟所有感官的事情,因為那裡連書都不讓你帶 ,也不能帶紙跟筆,等於說你不要做任何思考。他們有一個時間表:吃素食早餐、打坐、早晚的共修的時間,要聽一些跟佛經有關的東西。我一進去之後,滿被嚇到,因為那裡是一個「觀因寺」,原以為是沒什麼宗教組織,重點是靜坐打坐,但是他還是會跟一些廟合作。
我有一篇小說其中女主角就是一個流亡者,有時候去一些廟裡面給一些香油錢就借住一個晚上。到了那邊之後,就突然驚覺我就是那個自己書中的女主角。有時候很奇怪你寫的作品像會預示自己未來的劇本。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棒的一個放空的過程,裡面的素食非常好吃,每天在裡面就是走來走去;每天午餐以後都會有一個放風的時間, 可以去洗衣服 、散步、為了不影響別人,你可以拉一點身體,在太陽底下圍牆旁邊走來走去、走來走去;其實有時候有點無聊就很想觀察所有能夠觀察的東西。於是就開始看廟裡面的牆上各種經文,每一個都找來念一下。最有感覺的是「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重點不是要明白語言的意義,而是每天用我會的語言,就是中文Mandarin 跟粵語重複唸很多次,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然後突然被粵語,我的母語廣東話那個聲音的美學驚豔到;我只有念粵語的時候才會有那個感覺。這個美感之中好像得到一種無法撇除的認同, 所以這一句子對我來說,想起來就像是一段很美的音樂。這個經驗一直在我腦中停留。
內觀出來之後,覺得好像是照了一個X-Ray,把你的毒或是你有什麼創傷、放不開的東西會突然在那時間炸出來,很明顯發現還沒有 get over或是某一件事情還沒有治好recover,像照了一個X光,但還是繼續生活,就是發現自己有一個東西卡在那邊。
D. 《過動公寓》得獎
出來沒多久,大概是四月左右,我之前投稿的《過動公寓》得了周夢蝶詩獎,之後就終出版了我的詩集。年底的時候就辦了一些發表會。
其實我是2021年底畢業,這本書是2023年底出版,整個骨架跟主要的概念其實都是在花蓮東華大學這個地方寫成的,其他可能還有後來去臺北的一些景點。很多詩都是寫在一個瞬間,好像是在迸寫。我後來就在思考什麼是一個瞬間?難道一個瞬間就等於這件事很廉價嗎?就是在思考這個事情的時候,發覺我當時能夠擁有那個瞬間,其實是包含了整個天時地利人和—在花蓮這個環境保護之下才能夠提供我這一個瞬間。如果沒有來花蓮可能我真的不會寫出什麼東西。
E. 關進錄音室
這本書出來之後,辦完新書發表會,我就就把自己關起來了兩次;不是內觀,是錄音室。
記得是過年前後的一段時間,有一個朋友有一個空間可以借給我使用,我就把自己關在這個錄影室裡面,以我所有會的語言—中文、廣東話跟我會的一兩句臺語,把整本書讀一遍。
那個錄影室的結構,一邊是你錄音或是表演的地方,另外一邊是有人隔著玻璃看得到你,幫你按一下紅色的錄音按鈕、 控制、監聽你的聲音等等;那個過程好像又回到小時候玩的那個玩具,一邊是say一邊是play,只是他變成一個很具體的版本。
當時是是過年,我在那邊住了幾天,每天一醒來 就是很茫然的對著那本書,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就是覺得我很需要做,把它化成一個聲音;每天醒來我就嘗試去做一些聲音的實驗。當時我還沒有什麼曲子、旋律的概念, 我只是衝進去,先用那個說話的方式處理,吸收一次,再吐出來。
F. 把音樂從名詞變成動詞
我錄音的時候已經開始上臺大音樂所一個學期的課,有一天音樂學的一個概念叫做Musiking就是「樂動」突然在我腦中出現;它是由一個社會音樂學家Christopher Small在他的《Musiking》這本書裡面提出的:在古典音樂,我們最在意的就是樂譜,好像樂譜是最神聖的,後來的一些音樂家或指揮家都是在回頭詮釋那個作曲家當時的intention。在我們這個時代,對音樂的想像可能是一個專輯、一個CD、 一個黑膠或是一首曲子,一個streaming的album 就是代表音樂。但其實,我們忽略了很多當中的各種元素, 其實音樂最重要的是 彈奏音樂的那個人。 所以他提出了Musiking 就是把音樂 從一個名詞變成一個動詞; 在意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研究家跟觀眾的關係ˎ 表演者跟那個空間聲音的關係ˎ跟 他社會的一種關係ˎ 還有你實際進去演的那種經驗。最重要的不是那個很物質的存在, 尤其是古典音樂就是把樂譜看得很重要, 就是所有東西都有一個可以指認點,但其實世界上很多的音樂可能是口耳相傳的甚至是不願意被樂譜記載。有些音樂人可能會覺得如果把我的音樂記載到一個樂譜上, 其實是把我的音樂鎖死了。 所以他就提出很多東西都可以是一個躍動, 是一個music game。在洗澡的時候唱一首喜歡的歌也是在躍動, 聽歌的時候跳舞, 也是在參與這個躍動, 你把一個黑膠放在一個唱盤上, 你看著它震動, 也是一種躍動, 甚至你參加一個音樂演唱會, 賣票給你的那個人也是躍動的一部分。所以對我在音樂創作的啟發, 也是做完一個專輯不等於說那個音樂就完成了, 因為你永遠都可以在現場重新去詮釋它, 你其實可以一直變動它。所以那個專輯做完以後, 其實就只是當下這個時期的一個版本而已。
G. 文學可以躍動嗎?
回到文學, 我們可能會一輩子都在雕琢一個文本的完美, 所以要寫完, 寫到最精緻才是完成了。一天我在等紅綠燈的時候就在思考, 文學做完之後它就死了嗎? 文學還有什麼躍動的可能? 突然想到這句話, 我就把它寫在我帶的一本書後面的白頁上--文學作為躍動。文學可以怎麼動? 我的詩集是叫《過動公寓》, 它還可以怎麼動呢?
在錄音室錄完之後, 我回家感覺好像被一個念頭逮捕, 或是被卡住的一個感覺, 不得不回應它, 好像開了一張空頭支票, 我就找我的朋友幫我設計一個海報, 我想了一個題目: 過動巡迴, 就是巡迴過動本身; 這個巡迴就是我的書的一個過動的形式。 所以它從一個書本, 好像是一個物件, 我又把它從墳墓裡挖出來, 讓它動一下。那時候我在錄音室錄了一些碎片, 一些實驗的零件clip, 還不能夠完全作為一個音樂的元素。我為什麼會說好像是一個空頭支票? 就是其實那時候 我根本就還沒有寫完我的專輯, 然後這個tour最大的原因不是為了要宣傳, 而是我想要透過這個過動的過程把一個作品生出來。每次面對一個deadline, 我都會為了那場演出做一些新的曲子, 然後結束之後收到一些回饋, 那個回饋又會成為再投入下一場的養分。
H. Poetry recital
當時Tour改了一個名字叫英文的poetry recital。為什麼是poetry recital? 在古典音樂裡面有Cello recital 或是Oboe recital, 也 就是一個主要的樂器獨奏, 它可能會有一些伴奏, 但主要是樂器獨奏家的一個演出。然後我就想詩可不可以也是一種recital? 所以我把那個poetry置換在那個樂器的位置, 於是我就說這是一個poetry recital; 那個詩歌本身就是樂器, 我的人聲也是我的樂器; recital這個英文也有一個朗讀背誦的意思, 是一個雙重的意涵: 一個是詩歌作為樂器; 一個是詩歌的朗讀。很多時候我也在思考, 可能還沒思考完關於Michael Bond這個東西的象徵意義, 因為它好像是代表某種權利-- 就是你有一個麥克風, 你有一種話語權。 但某些時候在音樂之中, 其實你就只是把一個音軌錄下來而已, 就只是一個很物理性的存在, 麥克風在你不要想權利關係的時候, 它其實也只是一個分享擴音的平臺, 一個媒介。所以對麥克風的象徵,我還在思考。
I. Queer Temporality 酷兒時間性
我先講一下, 我是先做完一個出版之後, 又把自己關進錄音室; 這就要提到一個概念叫 Queer Temporality, 就是酷兒時間性, 是一個酷兒學者也是性別學者Jack Halberstam提出的。
他就說其實這世界上存在一種非異性戀規範的生命時間,就是如果可能主流的人生的生命 有一個潛在的劇本就是說你出生長大, 然後念書畢業找你的伴侶結婚生小孩, 生小孩之後你事業再上一層樓, 再生一個小孩, 然後你老去, 就是一個大眾的ˎ 最典型的一種時間規範。Jack Halberstam就提出酷兒時間性, 就是酷兒可能活在另外一種生命時間, 它不是一種進步論的, 不是說你怎樣一路往前。 其實人生本來就不是這樣, 你會樣反轉, 本來去這邊, 然後你還要退後十步, 好像在跳那個Tango。這個概念不只是給酷兒去思考, 也是一種生命的可能。 對於酷兒來說 他成長以後就要面對要不要跟他家人出櫃? 這也是他生命的一種時間, 可能會可能不會; 然後講完以後對他的家庭帶來怎麼樣的波紋等等。酷兒的時間性的非線性, 就讓我覺其中得詩好像也是這樣跳來跳去, 我今天想那詩會不會也是一個酷兒空間? 可以有一種不一樣的內在邏輯在裡面。
J. 詩專輯製作過程
我會提到酷兒時間性, 是因為我回頭發現, 我的整個詩專輯的創作計畫, 好像是完全走在一個可以說是錯誤或者不尋常的時間脈絡上。
一般來說, 做一個專輯是先把歌寫完, 進到錄音室錄音, Mixing後製之後, 就進入一個 Album發表, 有一個Tour 去宣傳它。而我的作法是相反的或是錯的, 我是先出版了一本書之後, 把自己關在一個有點奢侈設備的錄音室裡面, 然後我在裡只是錄了一些元素, 離開錄音室之後, 我才開始寫歌準備我之後的 Poetry Recital Tour。Tour結束之後, 我需要整理所有材料; 所以是每次表演完之後又回頭再做一些聲音的創作。我發現我最舒服的狀態在我自己的家裡, 把門關窗起來, 好像是一種密室的奮鬥。
所以後來就是寫完之後, 就在家裡錄音, 之後在作品發布之前先做一個聆聽的preview導聆會, 最後才做一個album release。 但是我做完這一個album之後, 卻沒有接著做一個 album release跟tour, 所以我就在想, 我的這個時間線到底是什麼? 所以那個tour對我來說就是我的實驗trial and error的 一個必然的過程, 其實是為了製造出一個新的作品。
我就在想我是不是有點做錯? 跟一個理想的行銷路徑有點迂迴。
K. 現場觀賞Poetry Recital Tour幻燈片與聆聽作品
a. 走來走去: 這首詩其實是我剛來東華大學沒多久的時候, 可能就也沒有覺得自己要寫詩的時候寫的一首詩。那時候住在擷雲莊, 在那邊走來走去沒有看到幾個人, 好像進入了另外一個時空; 也是我在花蓮感覺好像活在自己的時間裡面, 是我在花蓮那時候的感受。到現在我還是覺得這首很無意識寫的一個作品, 雖然它很簡單, 但好像蠻能夠代表我自己的一個狀態, 或是我的香港同代人的一個狀態, 就是這樣,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不一定是固定的, 是可以離開的。我有時候覺得在一個走來走去的變動之中, 身體在動的時候它也會啟發你的腦袋。更矛盾的時候是搭飛機的時候, 沒有網路, 你也只能夠在你狹隘的位置中 ,但是那個飛機正在移動, 對我來說, 移動與不動之中卻是最大的安全感所在。
b. 第一場香港一所舊的公寓, 下午三點鐘。
c. 第四場臺南—身邊是一位視覺藝術家, 在香港幫我做整場的設計跟一些移動的視覺。
d. 臺南一個劇場--很自發性很DIY的空間, 非常便宜的價格 讓你在這個空間裡試驗 。結束之後, 大家就在那邊聊天, 在黃燈的環境之中繼續回想, 給我一些Feedback。
e. 在鹿港一個朋友的小院子裡面—很快搭出一個舞臺。如果在一個詩的空間裡面, 我們可以押韻, 可以不押韻, 然後整個活動下來我自己覺好像是一次一次我透過事件去押韻; 一個事件會引發另外一個事件, 一個事件會啟發另外一個事件, 一首歌會啟發到另外一首歌的過程。
L. 不停失敗與再嘗試
今年的六月就是網路發表了這個詩專輯之後, 收到臺灣詩學的一個期刊, 問我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作品同時結合了文字跟音符, 若刪去其中一個, 還能夠打動讀者, 你覺得它還有存在必要嗎? 這個問題在整個過程裡面一直問我自己, 所以我就說, 創作應該就是一個不停的失敗, 一個嘗試, 你不停思考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而且你應該要這樣不停的問你自己為什麼你要做這個媒介? 為什麼你要用這個元素在小說裡面? 為什麼是這個場景? 為什麼是這個對白? 為什麼這個人會講出這句話? 這句話是那個人物講的還是你在講的? 會不會整本書讀起來是你的聲音而不是那個角色的聲音。 這好像是創作過程, 不停地經歷的過程, 因為它就是藝術的本質。我從一開頭就在問, 一直試著回答: 用不同的本質, 不同的詞, 用書寫, 用打字, 用畫畫, 都試著去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做一個作品的初衷, 跟做到後面是會不停的變的。它就是一個跟隨著人生的不停的經驗跟體悟。
M. To Home
如果說我最開始為什麼要做這個作品? 其實在我腦中想起來一個很基礎句子: 我想要go home, 就是回家。但是什麼是是回家? 有一部分可能是 我想要回到一個我喜歡做聲音的這件事情上; 另外一方面, 我想要重新用我的身體, 因為錄音是一個非常的體力勞動的事情, 你要不停的喝水, 不停地動用你的元氣。
還有就是, 我在那個內觀營之中, 我跟那句經文(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的對話, 就突然發現, 原來我還是很喜歡廣東話這個聲音的美學, 很想重新回到這個語言裡面。可能我日常生活中不常用這個語言, 它已經變成是一種有距離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我想要回到這個語言, 透過我朗讀自己的詩, 好像企圖是一個和解。這裡有一個我做的鑰匙圈, 我做的原因是它釦著就是你的家, 就是to home。
N. 文字+聲音
我是其實是想要實驗「文字」跟「聲音」一加一 混在一起之後, 它會變成什麼? 我很好奇這個寫式。另外一點就是, 為什麼是一加一等於一 ? 現在很多人都會講「文學」跟「音樂」的跨域, 我不會用這個詞, 因為我們文學的源頭其實可能是「聲音」 , 因為本來story telling 敘事都是口耳相傳的一個活動, 只是有了紙跟印刷出現以後, 這個說故事的形式, 變成很個人化 一對一的一個相逢, 而不是一個群體的活動。我的思考不是一個變異, 而是一種還原; 不是什麼跨域, 而是這兩個東西本來就是在一起的, 只是後來它分開了, 所以我現在把它回到一起。這樣, 我不是一加一等於一 , 我不知道有沒有答案? 我不停的提問跟回答。如果大家有一些想法, 也可以跟我分享。
O. 啟發製作的點
2023年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突然很迷古老遠古的希臘女詩人Sappo; 傳說中她曾經寫過一萬多句詩篇, 但是後來這世界上能夠找到的都是她的詩的碎片, 剩下有記載的只有六百多句; 這六百多句之中都是碎片化的, 能夠完整拼湊起來的就只有一首。 她其實也是一個我們現在說的lesbian 就是女同志這個詞的源頭, 因Sappo曾經住在希臘Lesbo。當時在那麼古老的時候, 詩裡面有很多情慾的流動, 尤其是女跟女之間, 甚至你可以覺得是多邊戀的一個痕跡在裡面。她分享詩的方式是她拿著一個萊雅琴, 她的詩其實就是她的歌詞; 那時候可以說是非常前衛。 所以我就找到不同的翻譯來看, 然後我就覺得那時候啟發我很多。
Ann Carson 另外一個詩人, 翻譯過她所有的詩, 最近有一個中文簡體字的翻譯版《 If Not Winter 》,就是保留Sappo碎片化寫詩的方式; 總之很多人都會說 Sappo是個詩人, 女詩人等等; 但是Ann Carson的做法是從一開頭就寫Sappo其實是一個音樂人, 她的詩就是歌詞 Composed to be sung to the lyre. 但是下一句就是很聳動, 就是「所有的音樂都消失了」, 所以我們只能夠想像她這樣的一個存在; 還有, 如果她的音樂還在的話, 她的聲音會是怎樣的? 所以這可能也是啟發我的一個點: 去想像一個「詩的音樂」會是怎樣?
講題∣ 放一支麥克風在腦中:詩的發聲可能
主持人∣ 張寶云老師
日期∣ 2025.12.05
地點∣ 人一第三講堂(C109)
【演講紀錄∣劉柏萩】
王和平小時候玩過一種玩具,只有兩個按鍵say和play,大概可錄製六秒的聲音,長大後,變成一顆紅色錄音按鈕,她說,錄音是一種魔法,當我們在聽自己錄下的聲音,是會存在於當下,不是過去或未來。
在工作一段時間後,參加內觀營,一進入就先收手機,也不可以書寫和閱讀,與人交流也不被允許,在這樣的場所,感官會全部打開,你會看見世界的擾動,靜坐、散步,一段經文她反覆念誦,「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而且是用廣東話,她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母語是這麼美,句子的意義是什麼,她不管,聲音才是感受的主體。
《過動公寓》作為一本詩集出版,講者把自己關起來兩次,她想要把詩集錄下來,借用朋友的工作室,不斷的嘗試,用自己會的語言錄製,像是回到小時候玩玩具的樣子,裝備升級,本質上是相同的。
王和平在唸音樂所讀到「樂動」,社會音樂學家Christopher Small於1998提出,他把 Music (名詞) → Musicking (動詞),把音樂變成一種帶有社會性與互動性的關係,音樂給觀眾的感覺,播放黑膠的唱片震動,「樂譜是死的,音樂是活的」,作品的當下已被完成,但是經過傳播解讀,音樂正在流動,於是講者開始思考,那文學呢?文學可以樂動嗎?如果文學也可以動,那過動公寓怎麼動?
她首先設計了海報,規劃幾場演出,為這個未完成的作品做了一場實驗,在得到觀眾反饋後修改,也逼自己去完成它,她總覺得她開了空頭支票,因為她的作品還沒完成,卻又要表演給大家看。
《怪咖啡因》的製作不像傳統專輯的出產,她是在不斷的嘗試與失敗之中,得到一個實驗性的詩專輯,而這正是藝術的本質,創造,本來就是無止盡的嘗試,似乎想要突破某種框架,從本來想要to home回歸自身,轉向為聲音的純粹,作為不懂語言的聽者,我們透過聲音的表演,來轉譯為我們了解的,成為音樂。
【演講紀錄∣賈美玲】
一. 開場:
我的角色或是我的任務是一個講師 ,但是回到我自己的日常, 其實我就是一個不停的失敗又嘗試, 又失敗又嘗試的一個創作者而已。今天這個機會想要分享我自己最新作品裡面的一些思考、满足跟我最近可能在想什麼等等,希望也可以引發你們一些思考。
二. 講座內容:
你們一開頭聽到的那首歌叫做《敬我們的過動公寓》是我詩專輯《怪咖啡因 BLAME IT ON THE CAFFEINE》的主題曲, 也是今天的題目。 這個詩集是從我的《過動公寓 》詩集中摘取了15首詩分別做成曲子,再讓它去跟聲音做一個碰撞; 我好像是重新讀一遍ˎ身體再吸收一次,然後吐出一個新的東西出來。最後發表的形式就是一個卡帶。
為什麼是卡帶?
我看著它在錄音機轉的時候就覺得好像我把我所有的迂迴、 我的內向都捲在裡面; 看到捲的時候, 好像是看到一種時間的流動在裡面 。
A. 回顧之前兩堂課:
上兩堂課, 我跟大家讀了一些詩, 也分享各自的詩觀; 然後我也跟大家一起從身體出發, 比較直覺性的詩的工作坊 , 就是我放了一些節奏, 發了卡夫卡的《變形記》第一章文本給大家, 要你從一個現有的文字, 透過刪除去建構另外一種敘事的空間; 等於說你破壞了現成的文字, 然後拿回你自己的聲音和自己的敘事空間。
我們還讀了《陰道獨語》這個劇本的一些片段, 我覺得它整本書就是一首詩,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比一個生命的誕生更詭異更像詩; 就是從一個空間來到另外一個空間。「陰道」這個東西它本來明明就只是一個人體的器官, 但在我們的社會裡面卻好像是一個不能明說的禁忌, 但是它又是一個生命的出口, 所以我總覺得這好像跟詩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就帶大家讀了一些它的文字。
上一堂課, 我們做了聆聽的練習--聽雨聲。大家在那五到十分鐘嘗試去聆聽跟分辨我們很熟悉的環境之中的聲音。 在課堂快結束之前, 我們Sound Walk 聲音步行; 一群人跟著同樣的節奏, 往同一個方向走。把意識放在聽覺上 , 看可不可以開啟一些別的感官。希望之後收到你們作業的時候, 可以看到大家當時的一個心態模樣。
所以, 其實上一堂課很多的東西都是來自於這本小書, 叫做《聽見聲音的地景》, 書裡面有很多聆聽的練習, 引導你想像最遠的聲音是什麼? 最近的聲音是什麼? 重新訓練我們的耳朵。
我們後來也提到藝術史之中的一種錯置, 一個邊界的問題. 一個音樂家John Cage有一個很有名的曲子《四分三十三秒》, 他請一個鋼琴家在臺上開啟一個鋼琴就坐下來, 然後什麼都沒做, 偶爾翻琴譜的葉子, 就在那邊坐了四分鐘, 之後結束。在那個過程中, 觀眾覺得很疑惑, 你要帶給我們什麼? 他其實想要argue的就是所有聲音都可以是一種音樂, 包括觀眾的煩躁, 或是人體一種觸摸的聲音, 所有的這些雜音都可以是音樂。從此整個音樂歷史改變 了許多。
我們也講到如果一個動作可以是一個雕塑, 一句話可以是一個指令, 一個事件的樂譜, 那詩它有什麼可能性? 就是在各種錯置或是媒體的邊界模糊之中, 「詩」它有什麼可能性? 除了文學獎或是現有的框架之下, 你還可以做一些什麼? 還有什麼更好玩ˎ更直觀或是刺激的東西?
我自己的詩觀, 一直以來都是滿簡單的, 就是想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讓悶住的聲音響亮; 不想生活的太有張力, 像這個路上悶住的喇叭裝置一樣。
B. 我的創作者身分。
這是我小時候的一個玩具。它上面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say, 一個是play。 你按下say就可以大概錄下六秒鐘的聲音或是空氣; 按play的時候它就會一直重播。 我非常的著迷放在嘴邊按say,再放在耳邊按play ,不停的重複;後來我發現這個小小的玩具好像是一種錄音軟體的一個原型。長大以後我還是追隨著那個紅色的錄音的按鈕; 這個按鈕有一個魔法就是你戴耳機按下去錄音的時候, 第一個聽到的人就是你自己。對我來說最療癒的地方就是彷彿可以讓時間停止, 在按下去的瞬間突然覺得過去不存在, 未來你暫時也不會想, 完全的活在那個當下, 關注接下來要做什麼, 現在要做什麼, 這是錄音對我來說的魔法。
C. 分享2023年的內觀經驗
2023年的時候我有一個比較長的假期,在臺灣參加了一個靜修營,就是10天的內觀;內觀就是你正式入營之後,沒收你的手機,你不能跟任何人講話,你會有室友,但是他們不鼓勵跟任何人有眼神的接觸,盡量不要跟人產生什麼緣分。如果我們上一次那個Sound Walk是開啟了一個聽覺的感官,我覺得那個內觀是一件開啟所有感官的事情,因為那裡連書都不讓你帶 ,也不能帶紙跟筆,等於說你不要做任何思考。他們有一個時間表:吃素食早餐、打坐、早晚的共修的時間,要聽一些跟佛經有關的東西。我一進去之後,滿被嚇到,因為那裡是一個「觀因寺」,原以為是沒什麼宗教組織,重點是靜坐打坐,但是他還是會跟一些廟合作。
我有一篇小說其中女主角就是一個流亡者,有時候去一些廟裡面給一些香油錢就借住一個晚上。到了那邊之後,就突然驚覺我就是那個自己書中的女主角。有時候很奇怪你寫的作品像會預示自己未來的劇本。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棒的一個放空的過程,裡面的素食非常好吃,每天在裡面就是走來走去;每天午餐以後都會有一個放風的時間, 可以去洗衣服 、散步、為了不影響別人,你可以拉一點身體,在太陽底下圍牆旁邊走來走去、走來走去;其實有時候有點無聊就很想觀察所有能夠觀察的東西。於是就開始看廟裡面的牆上各種經文,每一個都找來念一下。最有感覺的是「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重點不是要明白語言的意義,而是每天用我會的語言,就是中文Mandarin 跟粵語重複唸很多次,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然後突然被粵語,我的母語廣東話那個聲音的美學驚豔到;我只有念粵語的時候才會有那個感覺。這個美感之中好像得到一種無法撇除的認同, 所以這一句子對我來說,想起來就像是一段很美的音樂。這個經驗一直在我腦中停留。
內觀出來之後,覺得好像是照了一個X-Ray,把你的毒或是你有什麼創傷、放不開的東西會突然在那時間炸出來,很明顯發現還沒有 get over或是某一件事情還沒有治好recover,像照了一個X光,但還是繼續生活,就是發現自己有一個東西卡在那邊。
D. 《過動公寓》得獎
出來沒多久,大概是四月左右,我之前投稿的《過動公寓》得了周夢蝶詩獎,之後就終出版了我的詩集。年底的時候就辦了一些發表會。
其實我是2021年底畢業,這本書是2023年底出版,整個骨架跟主要的概念其實都是在花蓮東華大學這個地方寫成的,其他可能還有後來去臺北的一些景點。很多詩都是寫在一個瞬間,好像是在迸寫。我後來就在思考什麼是一個瞬間?難道一個瞬間就等於這件事很廉價嗎?就是在思考這個事情的時候,發覺我當時能夠擁有那個瞬間,其實是包含了整個天時地利人和—在花蓮這個環境保護之下才能夠提供我這一個瞬間。如果沒有來花蓮可能我真的不會寫出什麼東西。
E. 關進錄音室
這本書出來之後,辦完新書發表會,我就就把自己關起來了兩次;不是內觀,是錄音室。
記得是過年前後的一段時間,有一個朋友有一個空間可以借給我使用,我就把自己關在這個錄影室裡面,以我所有會的語言—中文、廣東話跟我會的一兩句臺語,把整本書讀一遍。
那個錄影室的結構,一邊是你錄音或是表演的地方,另外一邊是有人隔著玻璃看得到你,幫你按一下紅色的錄音按鈕、 控制、監聽你的聲音等等;那個過程好像又回到小時候玩的那個玩具,一邊是say一邊是play,只是他變成一個很具體的版本。
當時是是過年,我在那邊住了幾天,每天一醒來 就是很茫然的對著那本書,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就是覺得我很需要做,把它化成一個聲音;每天醒來我就嘗試去做一些聲音的實驗。當時我還沒有什麼曲子、旋律的概念, 我只是衝進去,先用那個說話的方式處理,吸收一次,再吐出來。
F. 把音樂從名詞變成動詞
我錄音的時候已經開始上臺大音樂所一個學期的課,有一天音樂學的一個概念叫做Musiking就是「樂動」突然在我腦中出現;它是由一個社會音樂學家Christopher Small在他的《Musiking》這本書裡面提出的:在古典音樂,我們最在意的就是樂譜,好像樂譜是最神聖的,後來的一些音樂家或指揮家都是在回頭詮釋那個作曲家當時的intention。在我們這個時代,對音樂的想像可能是一個專輯、一個CD、 一個黑膠或是一首曲子,一個streaming的album 就是代表音樂。但其實,我們忽略了很多當中的各種元素, 其實音樂最重要的是 彈奏音樂的那個人。 所以他提出了Musiking 就是把音樂 從一個名詞變成一個動詞; 在意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研究家跟觀眾的關係ˎ 表演者跟那個空間聲音的關係ˎ跟 他社會的一種關係ˎ 還有你實際進去演的那種經驗。最重要的不是那個很物質的存在, 尤其是古典音樂就是把樂譜看得很重要, 就是所有東西都有一個可以指認點,但其實世界上很多的音樂可能是口耳相傳的甚至是不願意被樂譜記載。有些音樂人可能會覺得如果把我的音樂記載到一個樂譜上, 其實是把我的音樂鎖死了。 所以他就提出很多東西都可以是一個躍動, 是一個music game。在洗澡的時候唱一首喜歡的歌也是在躍動, 聽歌的時候跳舞, 也是在參與這個躍動, 你把一個黑膠放在一個唱盤上, 你看著它震動, 也是一種躍動, 甚至你參加一個音樂演唱會, 賣票給你的那個人也是躍動的一部分。所以對我在音樂創作的啟發, 也是做完一個專輯不等於說那個音樂就完成了, 因為你永遠都可以在現場重新去詮釋它, 你其實可以一直變動它。所以那個專輯做完以後, 其實就只是當下這個時期的一個版本而已。
G. 文學可以躍動嗎?
回到文學, 我們可能會一輩子都在雕琢一個文本的完美, 所以要寫完, 寫到最精緻才是完成了。一天我在等紅綠燈的時候就在思考, 文學做完之後它就死了嗎? 文學還有什麼躍動的可能? 突然想到這句話, 我就把它寫在我帶的一本書後面的白頁上--文學作為躍動。文學可以怎麼動? 我的詩集是叫《過動公寓》, 它還可以怎麼動呢?
在錄音室錄完之後, 我回家感覺好像被一個念頭逮捕, 或是被卡住的一個感覺, 不得不回應它, 好像開了一張空頭支票, 我就找我的朋友幫我設計一個海報, 我想了一個題目: 過動巡迴, 就是巡迴過動本身; 這個巡迴就是我的書的一個過動的形式。 所以它從一個書本, 好像是一個物件, 我又把它從墳墓裡挖出來, 讓它動一下。那時候我在錄音室錄了一些碎片, 一些實驗的零件clip, 還不能夠完全作為一個音樂的元素。我為什麼會說好像是一個空頭支票? 就是其實那時候 我根本就還沒有寫完我的專輯, 然後這個tour最大的原因不是為了要宣傳, 而是我想要透過這個過動的過程把一個作品生出來。每次面對一個deadline, 我都會為了那場演出做一些新的曲子, 然後結束之後收到一些回饋, 那個回饋又會成為再投入下一場的養分。
H. Poetry recital
當時Tour改了一個名字叫英文的poetry recital。為什麼是poetry recital? 在古典音樂裡面有Cello recital 或是Oboe recital, 也 就是一個主要的樂器獨奏, 它可能會有一些伴奏, 但主要是樂器獨奏家的一個演出。然後我就想詩可不可以也是一種recital? 所以我把那個poetry置換在那個樂器的位置, 於是我就說這是一個poetry recital; 那個詩歌本身就是樂器, 我的人聲也是我的樂器; recital這個英文也有一個朗讀背誦的意思, 是一個雙重的意涵: 一個是詩歌作為樂器; 一個是詩歌的朗讀。很多時候我也在思考, 可能還沒思考完關於Michael Bond這個東西的象徵意義, 因為它好像是代表某種權利-- 就是你有一個麥克風, 你有一種話語權。 但某些時候在音樂之中, 其實你就只是把一個音軌錄下來而已, 就只是一個很物理性的存在, 麥克風在你不要想權利關係的時候, 它其實也只是一個分享擴音的平臺, 一個媒介。所以對麥克風的象徵,我還在思考。
I. Queer Temporality 酷兒時間性
我先講一下, 我是先做完一個出版之後, 又把自己關進錄音室; 這就要提到一個概念叫 Queer Temporality, 就是酷兒時間性, 是一個酷兒學者也是性別學者Jack Halberstam提出的。
他就說其實這世界上存在一種非異性戀規範的生命時間,就是如果可能主流的人生的生命 有一個潛在的劇本就是說你出生長大, 然後念書畢業找你的伴侶結婚生小孩, 生小孩之後你事業再上一層樓, 再生一個小孩, 然後你老去, 就是一個大眾的ˎ 最典型的一種時間規範。Jack Halberstam就提出酷兒時間性, 就是酷兒可能活在另外一種生命時間, 它不是一種進步論的, 不是說你怎樣一路往前。 其實人生本來就不是這樣, 你會樣反轉, 本來去這邊, 然後你還要退後十步, 好像在跳那個Tango。這個概念不只是給酷兒去思考, 也是一種生命的可能。 對於酷兒來說 他成長以後就要面對要不要跟他家人出櫃? 這也是他生命的一種時間, 可能會可能不會; 然後講完以後對他的家庭帶來怎麼樣的波紋等等。酷兒的時間性的非線性, 就讓我覺其中得詩好像也是這樣跳來跳去, 我今天想那詩會不會也是一個酷兒空間? 可以有一種不一樣的內在邏輯在裡面。
J. 詩專輯製作過程
我會提到酷兒時間性, 是因為我回頭發現, 我的整個詩專輯的創作計畫, 好像是完全走在一個可以說是錯誤或者不尋常的時間脈絡上。
一般來說, 做一個專輯是先把歌寫完, 進到錄音室錄音, Mixing後製之後, 就進入一個 Album發表, 有一個Tour 去宣傳它。而我的作法是相反的或是錯的, 我是先出版了一本書之後, 把自己關在一個有點奢侈設備的錄音室裡面, 然後我在裡只是錄了一些元素, 離開錄音室之後, 我才開始寫歌準備我之後的 Poetry Recital Tour。Tour結束之後, 我需要整理所有材料; 所以是每次表演完之後又回頭再做一些聲音的創作。我發現我最舒服的狀態在我自己的家裡, 把門關窗起來, 好像是一種密室的奮鬥。
所以後來就是寫完之後, 就在家裡錄音, 之後在作品發布之前先做一個聆聽的preview導聆會, 最後才做一個album release。 但是我做完這一個album之後, 卻沒有接著做一個 album release跟tour, 所以我就在想, 我的這個時間線到底是什麼? 所以那個tour對我來說就是我的實驗trial and error的 一個必然的過程, 其實是為了製造出一個新的作品。
我就在想我是不是有點做錯? 跟一個理想的行銷路徑有點迂迴。
K. 現場觀賞Poetry Recital Tour幻燈片與聆聽作品
a. 走來走去: 這首詩其實是我剛來東華大學沒多久的時候, 可能就也沒有覺得自己要寫詩的時候寫的一首詩。那時候住在擷雲莊, 在那邊走來走去沒有看到幾個人, 好像進入了另外一個時空; 也是我在花蓮感覺好像活在自己的時間裡面, 是我在花蓮那時候的感受。到現在我還是覺得這首很無意識寫的一個作品, 雖然它很簡單, 但好像蠻能夠代表我自己的一個狀態, 或是我的香港同代人的一個狀態, 就是這樣,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不一定是固定的, 是可以離開的。我有時候覺得在一個走來走去的變動之中, 身體在動的時候它也會啟發你的腦袋。更矛盾的時候是搭飛機的時候, 沒有網路, 你也只能夠在你狹隘的位置中 ,但是那個飛機正在移動, 對我來說, 移動與不動之中卻是最大的安全感所在。
b. 第一場香港一所舊的公寓, 下午三點鐘。
c. 第四場臺南—身邊是一位視覺藝術家, 在香港幫我做整場的設計跟一些移動的視覺。
d. 臺南一個劇場--很自發性很DIY的空間, 非常便宜的價格 讓你在這個空間裡試驗 。結束之後, 大家就在那邊聊天, 在黃燈的環境之中繼續回想, 給我一些Feedback。
e. 在鹿港一個朋友的小院子裡面—很快搭出一個舞臺。如果在一個詩的空間裡面, 我們可以押韻, 可以不押韻, 然後整個活動下來我自己覺好像是一次一次我透過事件去押韻; 一個事件會引發另外一個事件, 一個事件會啟發另外一個事件, 一首歌會啟發到另外一首歌的過程。
L. 不停失敗與再嘗試
今年的六月就是網路發表了這個詩專輯之後, 收到臺灣詩學的一個期刊, 問我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作品同時結合了文字跟音符, 若刪去其中一個, 還能夠打動讀者, 你覺得它還有存在必要嗎? 這個問題在整個過程裡面一直問我自己, 所以我就說, 創作應該就是一個不停的失敗, 一個嘗試, 你不停思考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而且你應該要這樣不停的問你自己為什麼你要做這個媒介? 為什麼你要用這個元素在小說裡面? 為什麼是這個場景? 為什麼是這個對白? 為什麼這個人會講出這句話? 這句話是那個人物講的還是你在講的? 會不會整本書讀起來是你的聲音而不是那個角色的聲音。 這好像是創作過程, 不停地經歷的過程, 因為它就是藝術的本質。我從一開頭就在問, 一直試著回答: 用不同的本質, 不同的詞, 用書寫, 用打字, 用畫畫, 都試著去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做一個作品的初衷, 跟做到後面是會不停的變的。它就是一個跟隨著人生的不停的經驗跟體悟。
M. To Home
如果說我最開始為什麼要做這個作品? 其實在我腦中想起來一個很基礎句子: 我想要go home, 就是回家。但是什麼是是回家? 有一部分可能是 我想要回到一個我喜歡做聲音的這件事情上; 另外一方面, 我想要重新用我的身體, 因為錄音是一個非常的體力勞動的事情, 你要不停的喝水, 不停地動用你的元氣。
還有就是, 我在那個內觀營之中, 我跟那句經文(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的對話, 就突然發現, 原來我還是很喜歡廣東話這個聲音的美學, 很想重新回到這個語言裡面。可能我日常生活中不常用這個語言, 它已經變成是一種有距離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我想要回到這個語言, 透過我朗讀自己的詩, 好像企圖是一個和解。這裡有一個我做的鑰匙圈, 我做的原因是它釦著就是你的家, 就是to home。
N. 文字+聲音
我是其實是想要實驗「文字」跟「聲音」一加一 混在一起之後, 它會變成什麼? 我很好奇這個寫式。另外一點就是, 為什麼是一加一等於一 ? 現在很多人都會講「文學」跟「音樂」的跨域, 我不會用這個詞, 因為我們文學的源頭其實可能是「聲音」 , 因為本來story telling 敘事都是口耳相傳的一個活動, 只是有了紙跟印刷出現以後, 這個說故事的形式, 變成很個人化 一對一的一個相逢, 而不是一個群體的活動。我的思考不是一個變異, 而是一種還原; 不是什麼跨域, 而是這兩個東西本來就是在一起的, 只是後來它分開了, 所以我現在把它回到一起。這樣, 我不是一加一等於一 , 我不知道有沒有答案? 我不停的提問跟回答。如果大家有一些想法, 也可以跟我分享。
O. 啟發製作的點
2023年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突然很迷古老遠古的希臘女詩人Sappo; 傳說中她曾經寫過一萬多句詩篇, 但是後來這世界上能夠找到的都是她的詩的碎片, 剩下有記載的只有六百多句; 這六百多句之中都是碎片化的, 能夠完整拼湊起來的就只有一首。 她其實也是一個我們現在說的lesbian 就是女同志這個詞的源頭, 因Sappo曾經住在希臘Lesbo。當時在那麼古老的時候, 詩裡面有很多情慾的流動, 尤其是女跟女之間, 甚至你可以覺得是多邊戀的一個痕跡在裡面。她分享詩的方式是她拿著一個萊雅琴, 她的詩其實就是她的歌詞; 那時候可以說是非常前衛。 所以我就找到不同的翻譯來看, 然後我就覺得那時候啟發我很多。
Ann Carson 另外一個詩人, 翻譯過她所有的詩, 最近有一個中文簡體字的翻譯版《 If Not Winter 》,就是保留Sappo碎片化寫詩的方式; 總之很多人都會說 Sappo是個詩人, 女詩人等等; 但是Ann Carson的做法是從一開頭就寫Sappo其實是一個音樂人, 她的詩就是歌詞 Composed to be sung to the lyre. 但是下一句就是很聳動, 就是「所有的音樂都消失了」, 所以我們只能夠想像她這樣的一個存在; 還有, 如果她的音樂還在的話, 她的聲音會是怎樣的? 所以這可能也是啟發我的一個點: 去想像一個「詩的音樂」會是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