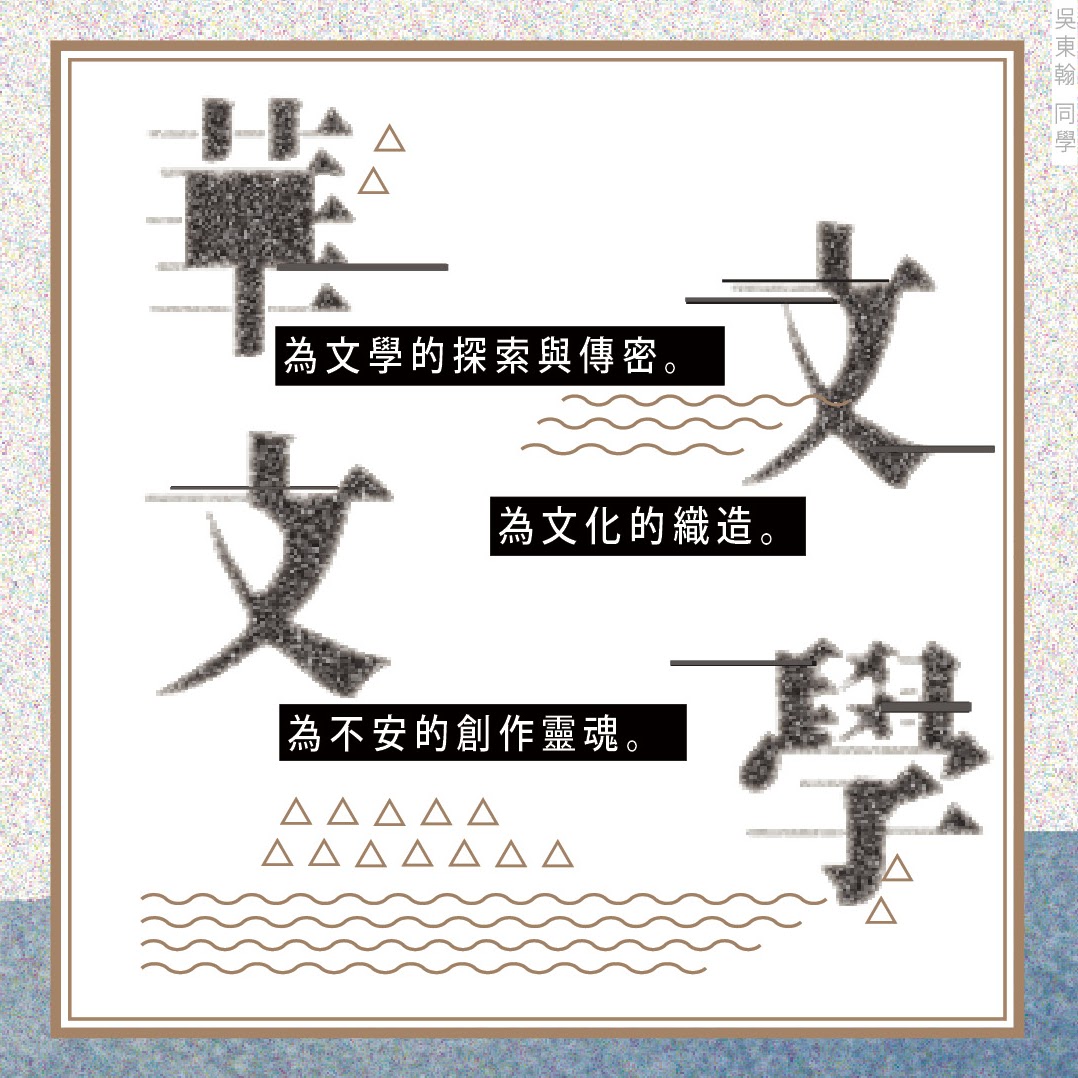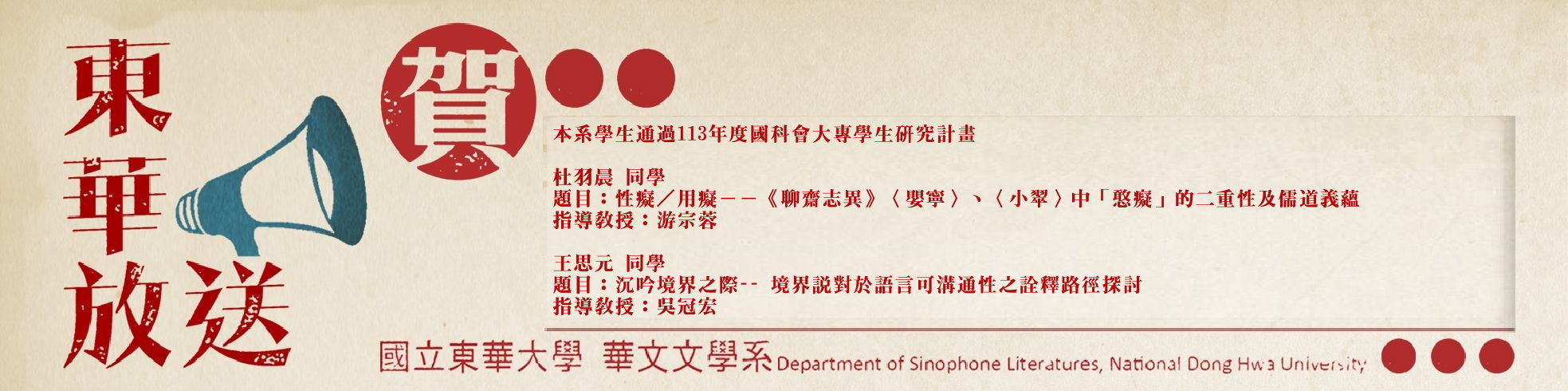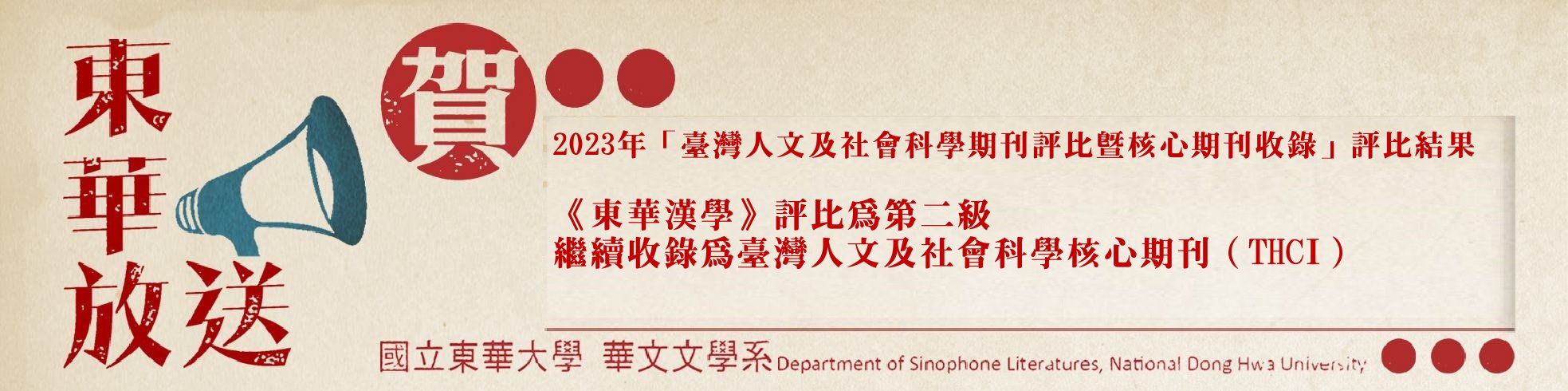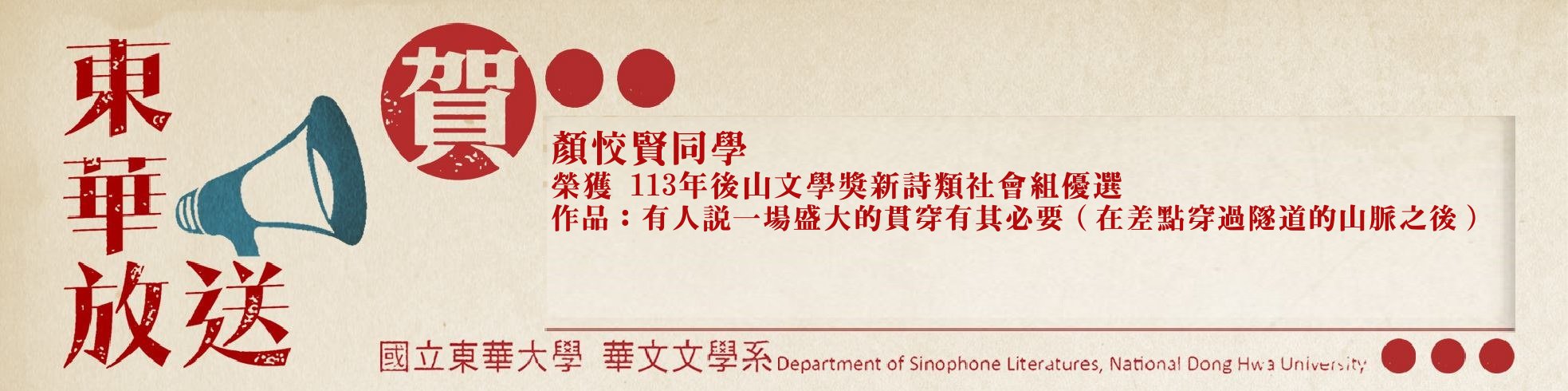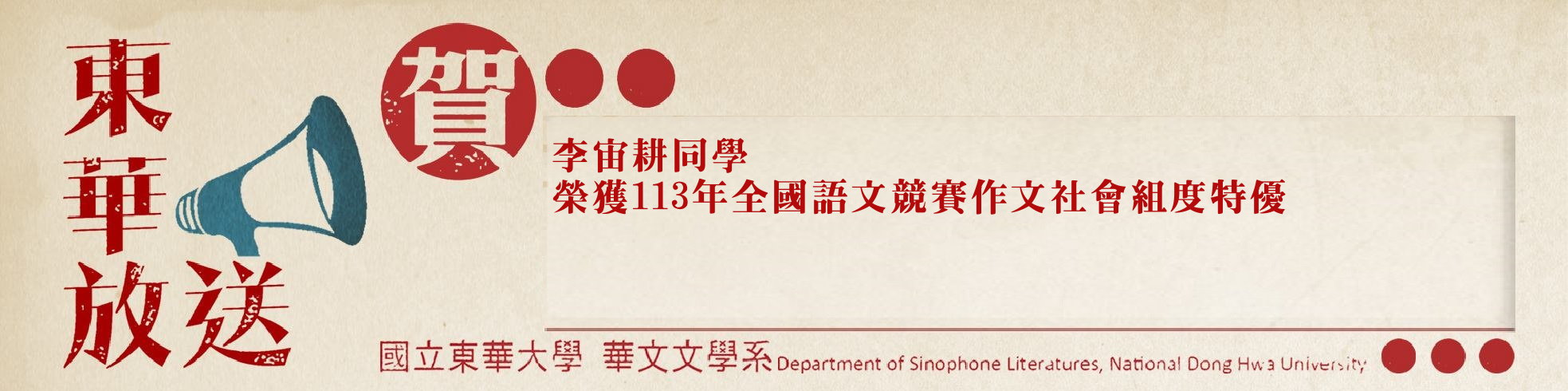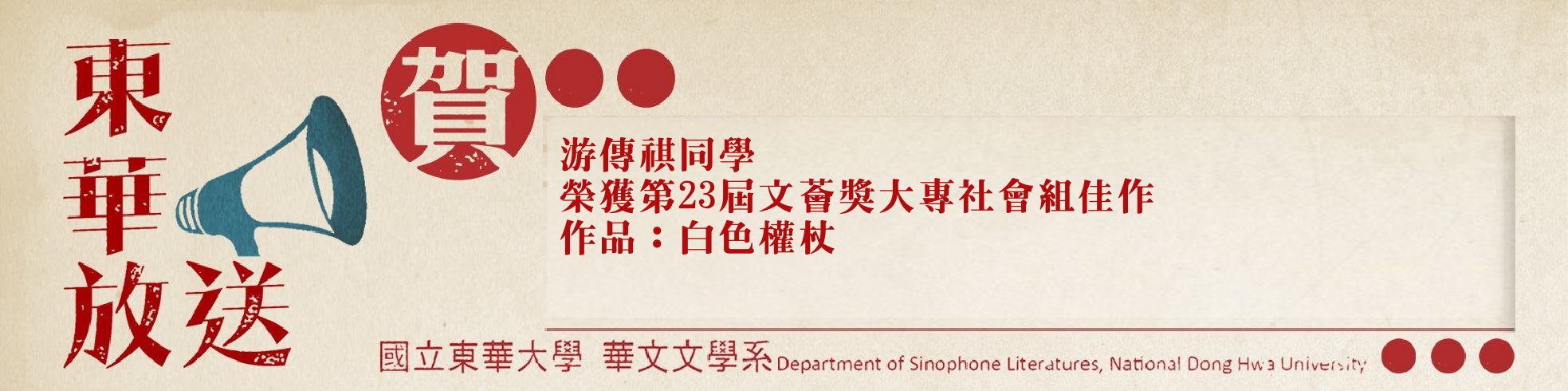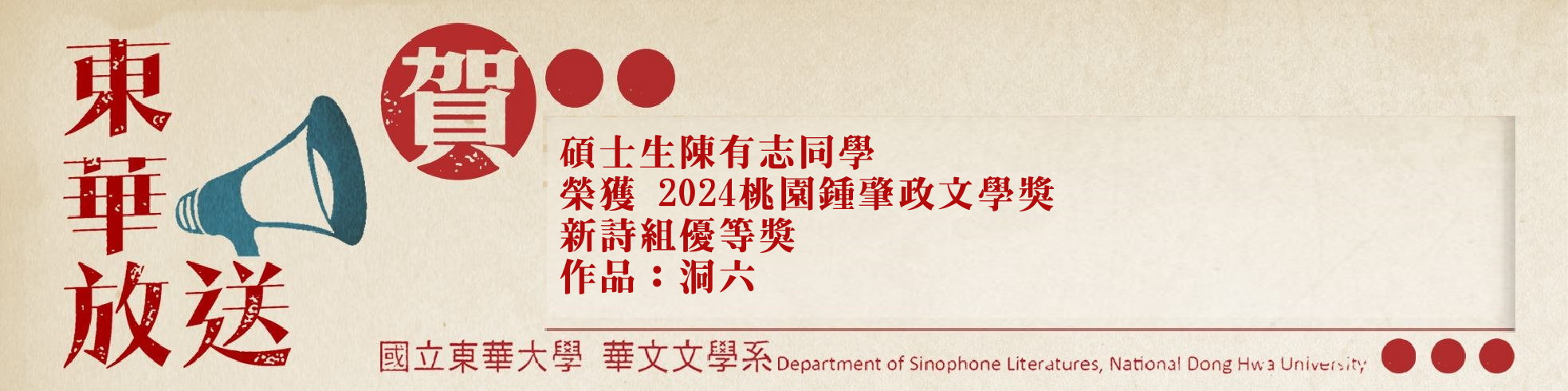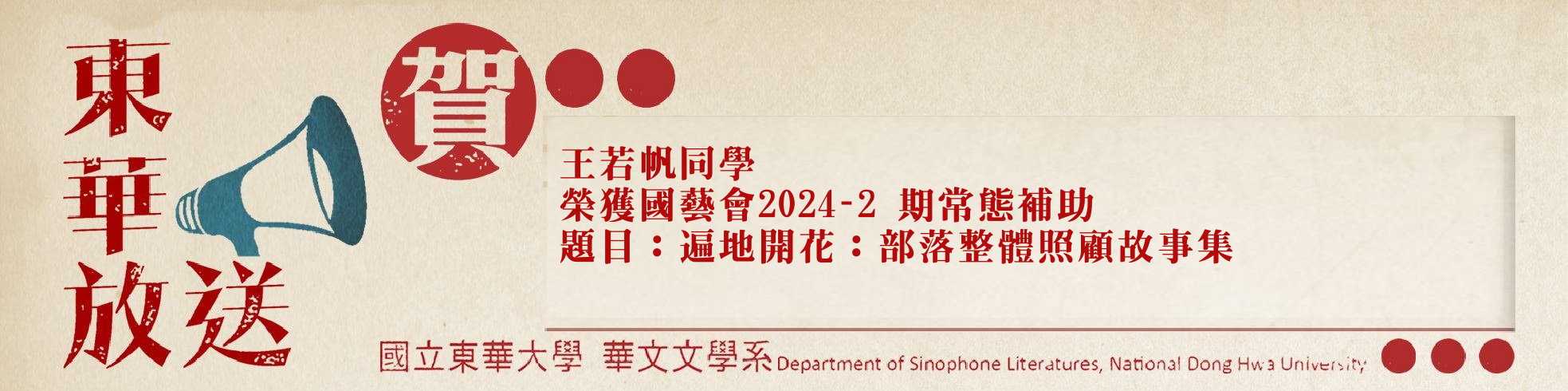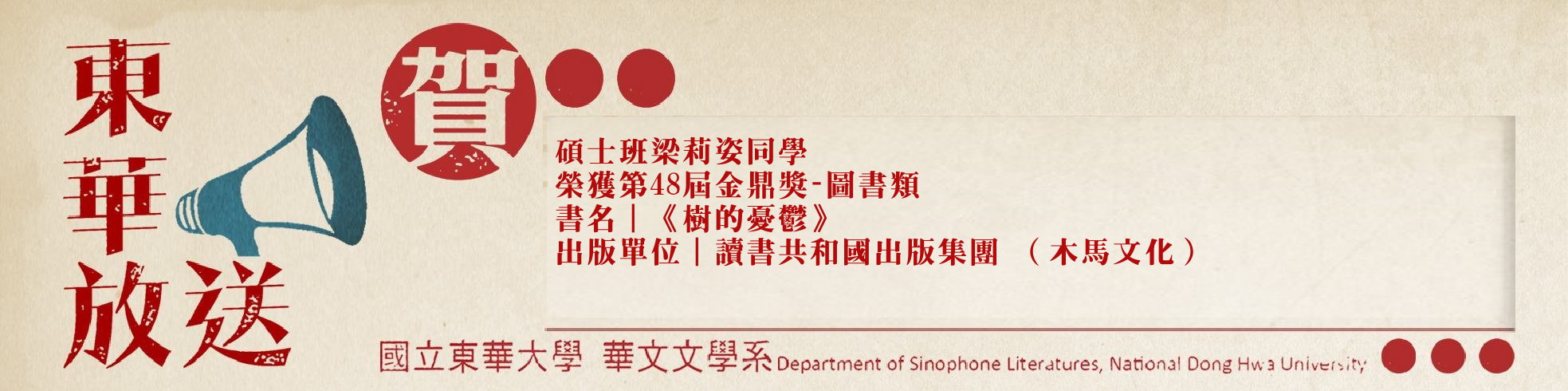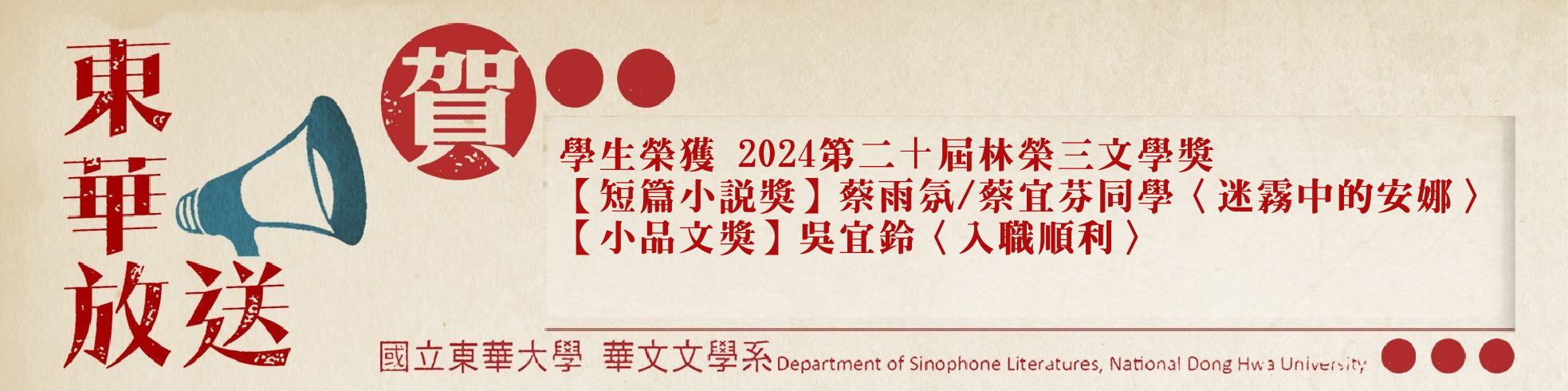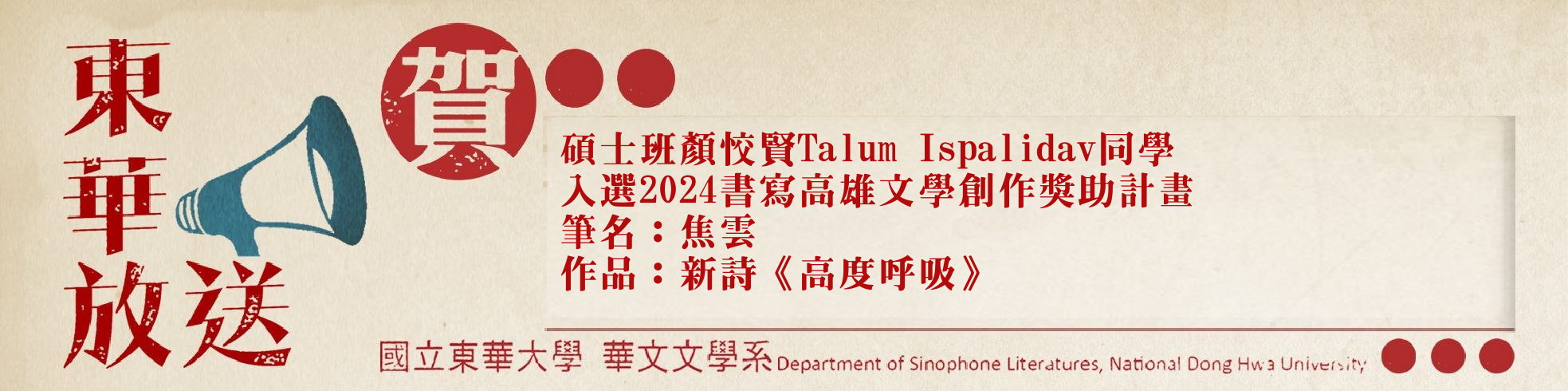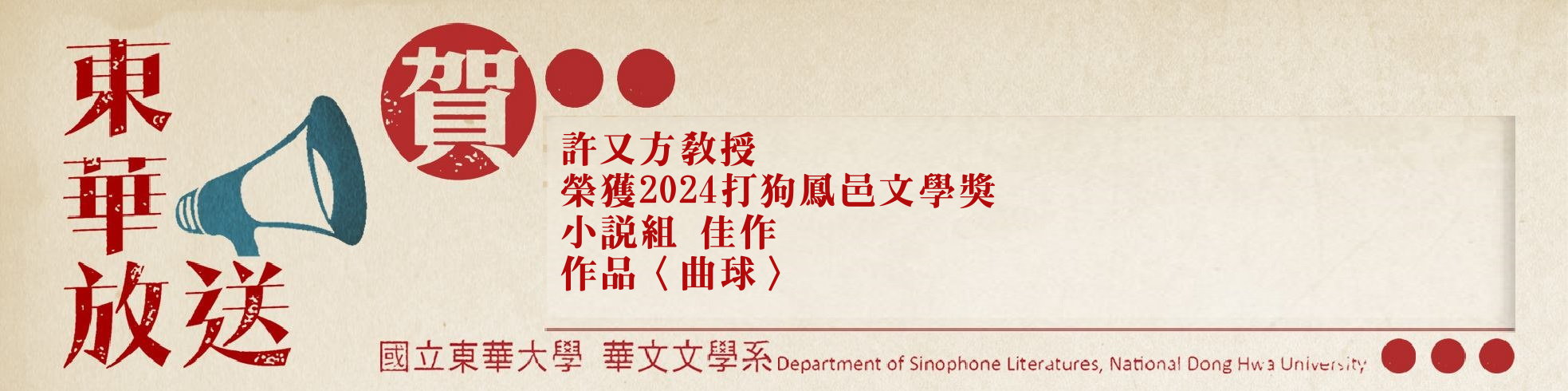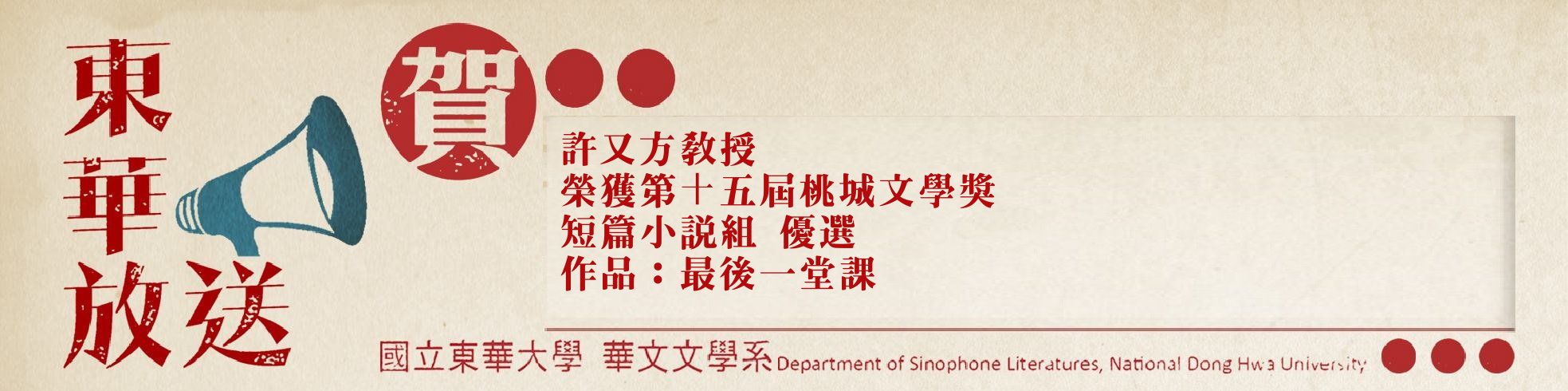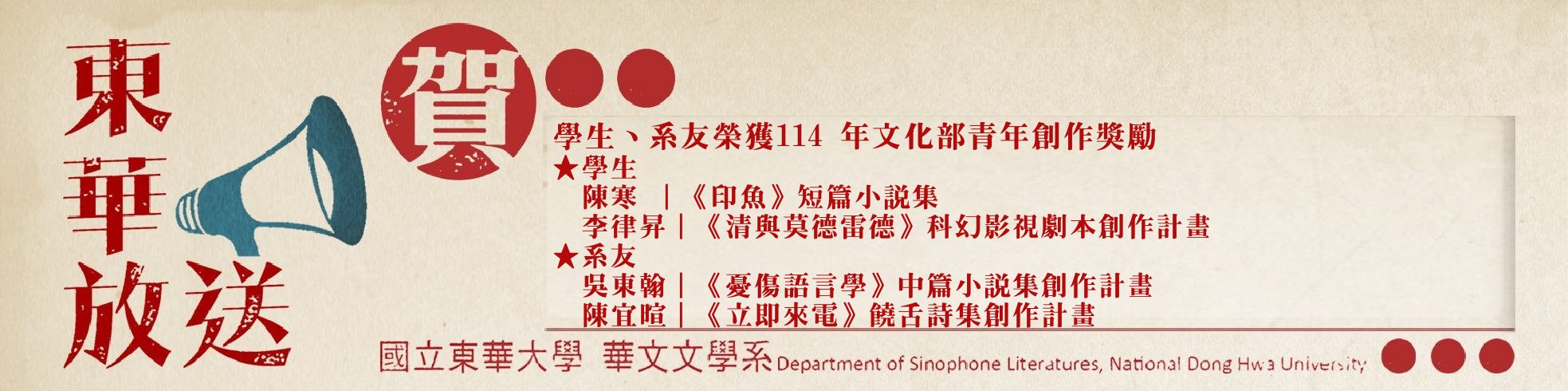演講心得【連明偉老師】|在場或不在場的地方
主講人∣ 連明偉老師
講題∣ 在場或不在場的地方
主持人∣ 張寶云老師
日期∣ 2024.05.03
【演講心得∣蕭舜恩】
這場演講從講題在場或不在場的他方的多義性開啟,他方的意義既是指涉第三人(在現場,發現自己永遠是第三方、局外人)、同時也是地理學意義上的異鄉。
令我印象深刻的,其一是講者在不同國家所從事的職業,包含飯店房務、廚師、桌球教練、木工。在台灣的時候也曾至銀行或是海運公司面試。可以在多地移動的人,都需要這麼大的轉換彈性嗎?
其二是講者在演講的時候所展現的閱讀系譜。連明偉談及自己的異國移動經驗,讓他關注阮越清、游朝凱等作家觸及移民的作品。在演講中也提到斑方登或是葛雷安.葛林筆下的第三世界,或是用太宰治《津輕》、葛雷安葛林《沒有地圖的旅行》談開始旅行的諸般動因。
其三是大量的自我追問。講師從班雅明兩種說故事的人的原型,引申到文學創作者的自問:難道你只有變成遊歷遠方的水手才能書寫嗎?或是從義大利作家paolo cognetti《八座山》的提問:誰學到最多呢?是去過八座山的人,還是攀上須彌山的人?去思考創作的深度與廣度。
甚至連畫作也能談,從皮爾波納爾Pierre Bonnard的畫(畫中人的身體線條邊界不明顯,彷彿融入周遭環境之中)談凝視的距離。一旦極端貼近某個物件或描摹對象時,眼睛所見的一切都會跟這個物件有關,但也因為貼得極近,因此失去精確性。連明偉認為這可以延伸到創作者對書寫對象的討論。究竟要如何觀看?遠觀還是近觀?
我想講師透過這場演講所展示的,未必是什麼心法或金科玉律,而是創作這件事,或許就是勢必得涉及大量的自我追問,過程或許很痛苦,可能也沒有答案,卻有可能從追問過程中,慢慢為自己打造出某種具質量的東西。
【演講心得∣王若帆】
連明偉老師的演講主題「在場(或不在場)」,在場談的是文本的地方性,B如何透過對地方的書寫來顯示、揭露某些訊息,這些「在場」的一切並非詳盡的如實描寫,而需要搭配適當的「不在場」──亦即文本的留白。
文本如何留白?他的可能性如此多樣。朱利安‧巴恩斯在長篇小說《回憶的餘燼》中,以「閃閃發亮的手腕內側」、「一坨精液在排水孔裡滾轉,沿著排水管被沖到幾層樓之下」、「一條莫名其妙的向後流的河」……等一系列不尋常的場景陳設,作為一種意義尚未被揭露的意象。這些他所提出來的意象、影像(畫面),在小說後頭開始進行解謎,留下的空白必須被填補,不然這樣的開頭是沒有意義的。
極簡主義的文學作品亦看重留白的技術。極簡主義強調理性、直線、幾何、對比。極簡主義的簡單是清晰有力的簡單,越是簡單的畫面,往往是透過越繁複的構思過程,來達到最後的藝術效果,越是純粹的造型元素的圖像,越是隱含繁複的感覺──單純是複雜的極致。
馬克吐溫曾經說過:「一本書會成功不是因為它裏頭寫了什麼,而是沒寫什麼」,這個說法有些偏激,但依舊有其成立的原因;我們再看另一個例子:契訶夫曾批評同時代的劇作家高爾基:我認為你缺乏自制力,你就像戲院裡不懂禮貌的觀眾,自顧大辣辣地表達自己的熱情,也不管會不會妨礙自己和其他人看戲。……尤其是你打斷對白,轉而描述自然景物的食物,更能看出你自制力有多缺乏。當讀者看到這些描述時,他們會希望句子簡潔一點,最後短上個兩、三行。
文學家之間的討論,促使我們審視自己的作品並思考:這些句子真的需要留存在那邊嗎?或是只是我們想表達自己視線與品味有多麼與眾不同?
類似的說法也曾被海明威提及:「每每見到所謂神聖、光輝、犧牲等字,或其他無用的表達,我便覺得困窘,裏頭根本看不到什麼神聖,理當光輝四射的東西也黯淡了。」神聖、光輝、犧牲等字眼,都是作者的意識型態,亦即海明威口中「根本不能入耳」的字句
海明威的「冰山理論」,亦是在講留白帶來的力量:「有八分之七留在水面之下,任何一清二楚的地方都應該刪去,只有看不見的地方才能鞏固這座冰山。」。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寫著「For sale:baby shoes, never worn.」這個著名的極短篇。透過這幾個字,我們在腦海中模擬了路邊廣告,讓讀者理解到因為戰爭、或者因為流產,孩子已經去世。這種作法直接取消了敘述的主體,用邊緣的角色/事物,讓讀者看見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個作者如果清楚自己在寫什麼,就可以略過那些他明確知道的東西不寫,只要作者的文本夠真誠,讀者也將能感受到那些事物。在路邊鞋子的例子中,透過非常簡短的字句,邀請讀者進行反推,進行主體性的建構,立體的情節就會出現在眼前,而正因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需要讀者來參與,讀者參與在其中,閱讀感受也會截然不同。
在「太陽依舊升起」中,男主角巴恩斯敘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也有如下描述的場景:
「討論這話題時,我挺坦然,過去可能有一兩次,我從絕大多數人的角度去看這回事,包含某些傷勢或缺憾總會變成笑柄,但對這些傷者來說,傷勢本人卻仍挺嚴重。……明明有那麼多地方可以受傷...我渾身捆著繃帶,已有人告訴他是情經過,他便來一場精采的演說:「你,一個外國人,一個英國人,奉獻了比性命更重大的事物。」
整段描述都沒有清楚提及他到底受到了什麼樣的傷害( 巴恩斯再也無法勃起 ),也省略了對戰場的描述( 造成他的傷勢來源 ),傷勢變成了恥辱和笑柄,這就是在水面下,非常洶湧的訊息。
沙林傑的「麥田捕手」,由兩至三日的遊蕩展開敘述,一個小孩子以漫遊、不斷罵髒話的方式對抗體制,他不談戰爭,但這位深刻歷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帶著「麥田捕手」初稿搶灘諾曼地的作家,也在這場遊蕩的背後放入一個未言明的大主題──戰爭所帶來的,許許多多的影響。如果可以理解這個意涵,就可以以理解小說本身。
喋喋不休或言簡意賅,都是一種藝術性的表達方式,我們可以基於風格或表達上的需求選擇喋喋不休,也可以選擇言簡意賅,也有可能造成的風險,都是可以嘗試的表達方式。
費茲傑羅曾在書信中批評沃爾夫:「世界上只有兩種作家:喋喋不休或言簡意賅。」沃爾夫對此回復:「誰管什麼福樓拜或不福樓拜,莎士比亞喋喋不休,梅爾維爾也愛喋喋不休。」
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世界上不存在客觀上「栩栩如真」的描述,詳細的描述和豐富的描述一樣,具有誤導作用。詳細的描述似乎可以告訴我們某些有意義的具體事項(關於某個角色、某個場景、這個世界),然而揭露的越多,帶來的樂趣就越少──越繪聲繪影,就越不真實。
安妮艾洛曾經在「如刀的書寫」中提出「文字如實物」的概念,當我們對物體用文字產生渲染,其實會產生失真,那些失真是我們的表演,使文字變成展演(透露的我們情情懷),表演的慾望並沒有錯,但要注意我們有時候會不小心表演太多,也因此失去了我們原本想要傾訴的內容、想溝通的意圖。文學想傾訴、想溝通的,常常會因為某些詩情畫意而造成誤解。
作家吉爾伯特說的更狠:「如果目標是栩栩如生的寫作,似乎只要一直寫一直寫,怎樣都行,作者是不是就被一連串密集意象帶來的重量,壓得變形、散開。接二連三的比喻,蓋住他們理應暴露的現實,例如『通訊與季刊湧進牧師的信箱口,就像尿液撒出母牛的外陰部』,這樣的寫作炫技又無異議。」我們去想像這樣的場景,其實是很生動的,但如果我們不斷這樣表達,只是凸顯了我們運用文字跳動的能力很好,但他跟我們真實要表達的意義之間其實會產生很大的距離。──困難的地方不在於炫技,而在於節制自己。
講題∣ 在場或不在場的地方
主持人∣ 張寶云老師
日期∣ 2024.05.03
【演講心得∣蕭舜恩】
這場演講從講題在場或不在場的他方的多義性開啟,他方的意義既是指涉第三人(在現場,發現自己永遠是第三方、局外人)、同時也是地理學意義上的異鄉。
令我印象深刻的,其一是講者在不同國家所從事的職業,包含飯店房務、廚師、桌球教練、木工。在台灣的時候也曾至銀行或是海運公司面試。可以在多地移動的人,都需要這麼大的轉換彈性嗎?
其二是講者在演講的時候所展現的閱讀系譜。連明偉談及自己的異國移動經驗,讓他關注阮越清、游朝凱等作家觸及移民的作品。在演講中也提到斑方登或是葛雷安.葛林筆下的第三世界,或是用太宰治《津輕》、葛雷安葛林《沒有地圖的旅行》談開始旅行的諸般動因。
其三是大量的自我追問。講師從班雅明兩種說故事的人的原型,引申到文學創作者的自問:難道你只有變成遊歷遠方的水手才能書寫嗎?或是從義大利作家paolo cognetti《八座山》的提問:誰學到最多呢?是去過八座山的人,還是攀上須彌山的人?去思考創作的深度與廣度。
甚至連畫作也能談,從皮爾波納爾Pierre Bonnard的畫(畫中人的身體線條邊界不明顯,彷彿融入周遭環境之中)談凝視的距離。一旦極端貼近某個物件或描摹對象時,眼睛所見的一切都會跟這個物件有關,但也因為貼得極近,因此失去精確性。連明偉認為這可以延伸到創作者對書寫對象的討論。究竟要如何觀看?遠觀還是近觀?
我想講師透過這場演講所展示的,未必是什麼心法或金科玉律,而是創作這件事,或許就是勢必得涉及大量的自我追問,過程或許很痛苦,可能也沒有答案,卻有可能從追問過程中,慢慢為自己打造出某種具質量的東西。
【演講心得∣王若帆】
連明偉老師的演講主題「在場(或不在場)」,在場談的是文本的地方性,B如何透過對地方的書寫來顯示、揭露某些訊息,這些「在場」的一切並非詳盡的如實描寫,而需要搭配適當的「不在場」──亦即文本的留白。
文本如何留白?他的可能性如此多樣。朱利安‧巴恩斯在長篇小說《回憶的餘燼》中,以「閃閃發亮的手腕內側」、「一坨精液在排水孔裡滾轉,沿著排水管被沖到幾層樓之下」、「一條莫名其妙的向後流的河」……等一系列不尋常的場景陳設,作為一種意義尚未被揭露的意象。這些他所提出來的意象、影像(畫面),在小說後頭開始進行解謎,留下的空白必須被填補,不然這樣的開頭是沒有意義的。
極簡主義的文學作品亦看重留白的技術。極簡主義強調理性、直線、幾何、對比。極簡主義的簡單是清晰有力的簡單,越是簡單的畫面,往往是透過越繁複的構思過程,來達到最後的藝術效果,越是純粹的造型元素的圖像,越是隱含繁複的感覺──單純是複雜的極致。
馬克吐溫曾經說過:「一本書會成功不是因為它裏頭寫了什麼,而是沒寫什麼」,這個說法有些偏激,但依舊有其成立的原因;我們再看另一個例子:契訶夫曾批評同時代的劇作家高爾基:我認為你缺乏自制力,你就像戲院裡不懂禮貌的觀眾,自顧大辣辣地表達自己的熱情,也不管會不會妨礙自己和其他人看戲。……尤其是你打斷對白,轉而描述自然景物的食物,更能看出你自制力有多缺乏。當讀者看到這些描述時,他們會希望句子簡潔一點,最後短上個兩、三行。
文學家之間的討論,促使我們審視自己的作品並思考:這些句子真的需要留存在那邊嗎?或是只是我們想表達自己視線與品味有多麼與眾不同?
類似的說法也曾被海明威提及:「每每見到所謂神聖、光輝、犧牲等字,或其他無用的表達,我便覺得困窘,裏頭根本看不到什麼神聖,理當光輝四射的東西也黯淡了。」神聖、光輝、犧牲等字眼,都是作者的意識型態,亦即海明威口中「根本不能入耳」的字句
海明威的「冰山理論」,亦是在講留白帶來的力量:「有八分之七留在水面之下,任何一清二楚的地方都應該刪去,只有看不見的地方才能鞏固這座冰山。」。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寫著「For sale:baby shoes, never worn.」這個著名的極短篇。透過這幾個字,我們在腦海中模擬了路邊廣告,讓讀者理解到因為戰爭、或者因為流產,孩子已經去世。這種作法直接取消了敘述的主體,用邊緣的角色/事物,讓讀者看見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個作者如果清楚自己在寫什麼,就可以略過那些他明確知道的東西不寫,只要作者的文本夠真誠,讀者也將能感受到那些事物。在路邊鞋子的例子中,透過非常簡短的字句,邀請讀者進行反推,進行主體性的建構,立體的情節就會出現在眼前,而正因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需要讀者來參與,讀者參與在其中,閱讀感受也會截然不同。
在「太陽依舊升起」中,男主角巴恩斯敘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也有如下描述的場景:
「討論這話題時,我挺坦然,過去可能有一兩次,我從絕大多數人的角度去看這回事,包含某些傷勢或缺憾總會變成笑柄,但對這些傷者來說,傷勢本人卻仍挺嚴重。……明明有那麼多地方可以受傷...我渾身捆著繃帶,已有人告訴他是情經過,他便來一場精采的演說:「你,一個外國人,一個英國人,奉獻了比性命更重大的事物。」
整段描述都沒有清楚提及他到底受到了什麼樣的傷害( 巴恩斯再也無法勃起 ),也省略了對戰場的描述( 造成他的傷勢來源 ),傷勢變成了恥辱和笑柄,這就是在水面下,非常洶湧的訊息。
沙林傑的「麥田捕手」,由兩至三日的遊蕩展開敘述,一個小孩子以漫遊、不斷罵髒話的方式對抗體制,他不談戰爭,但這位深刻歷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帶著「麥田捕手」初稿搶灘諾曼地的作家,也在這場遊蕩的背後放入一個未言明的大主題──戰爭所帶來的,許許多多的影響。如果可以理解這個意涵,就可以以理解小說本身。
喋喋不休或言簡意賅,都是一種藝術性的表達方式,我們可以基於風格或表達上的需求選擇喋喋不休,也可以選擇言簡意賅,也有可能造成的風險,都是可以嘗試的表達方式。
費茲傑羅曾在書信中批評沃爾夫:「世界上只有兩種作家:喋喋不休或言簡意賅。」沃爾夫對此回復:「誰管什麼福樓拜或不福樓拜,莎士比亞喋喋不休,梅爾維爾也愛喋喋不休。」
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世界上不存在客觀上「栩栩如真」的描述,詳細的描述和豐富的描述一樣,具有誤導作用。詳細的描述似乎可以告訴我們某些有意義的具體事項(關於某個角色、某個場景、這個世界),然而揭露的越多,帶來的樂趣就越少──越繪聲繪影,就越不真實。
安妮艾洛曾經在「如刀的書寫」中提出「文字如實物」的概念,當我們對物體用文字產生渲染,其實會產生失真,那些失真是我們的表演,使文字變成展演(透露的我們情情懷),表演的慾望並沒有錯,但要注意我們有時候會不小心表演太多,也因此失去了我們原本想要傾訴的內容、想溝通的意圖。文學想傾訴、想溝通的,常常會因為某些詩情畫意而造成誤解。
作家吉爾伯特說的更狠:「如果目標是栩栩如生的寫作,似乎只要一直寫一直寫,怎樣都行,作者是不是就被一連串密集意象帶來的重量,壓得變形、散開。接二連三的比喻,蓋住他們理應暴露的現實,例如『通訊與季刊湧進牧師的信箱口,就像尿液撒出母牛的外陰部』,這樣的寫作炫技又無異議。」我們去想像這樣的場景,其實是很生動的,但如果我們不斷這樣表達,只是凸顯了我們運用文字跳動的能力很好,但他跟我們真實要表達的意義之間其實會產生很大的距離。──困難的地方不在於炫技,而在於節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