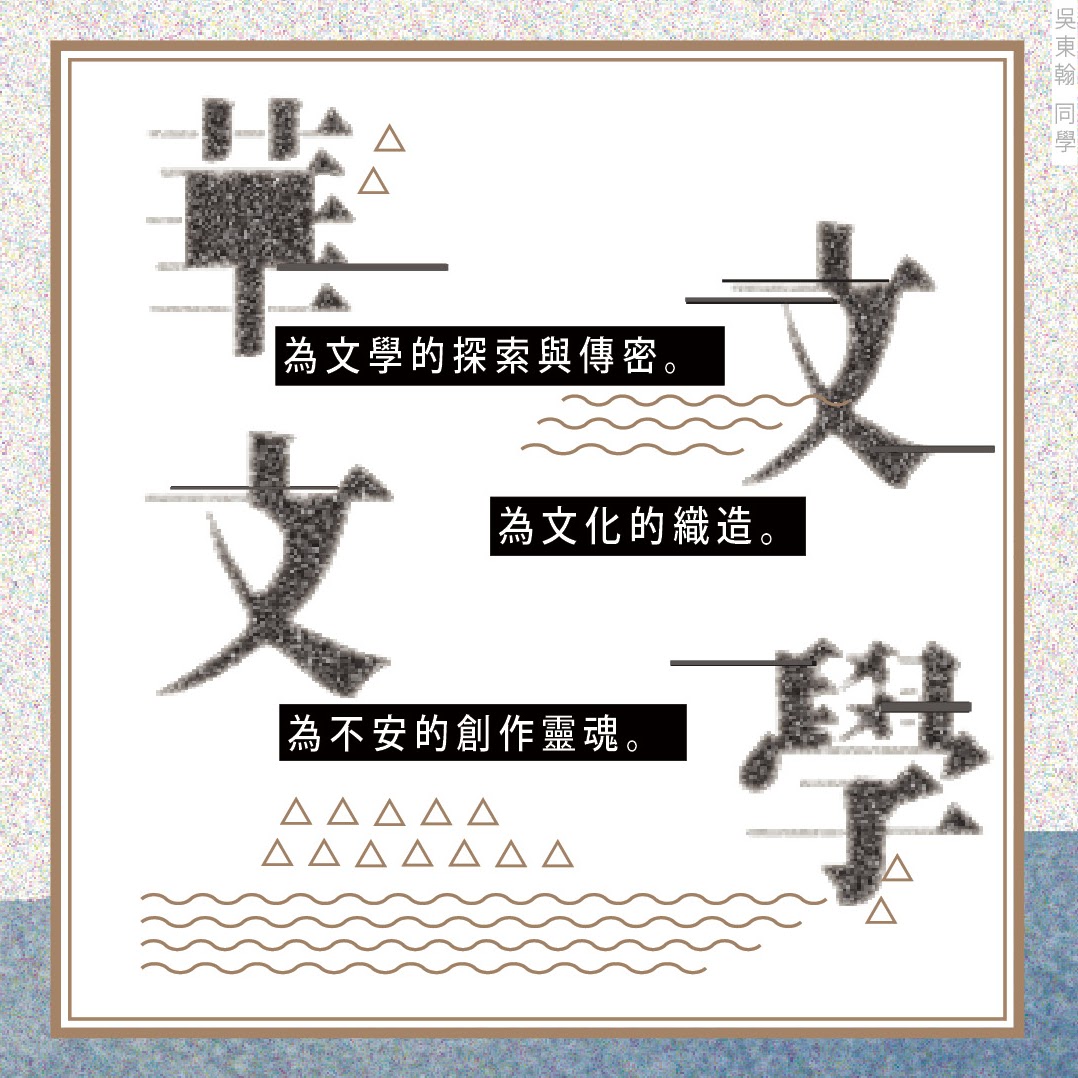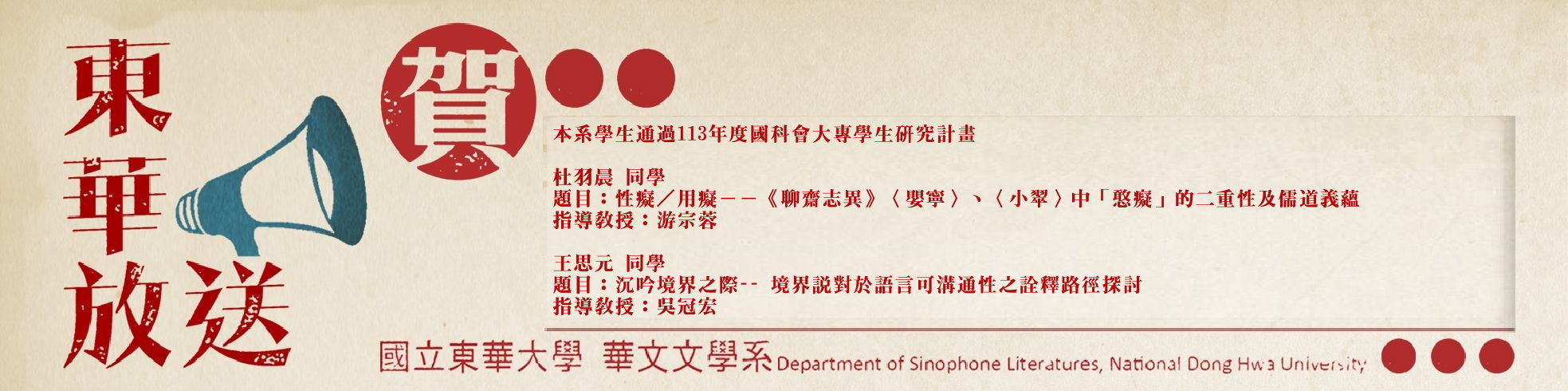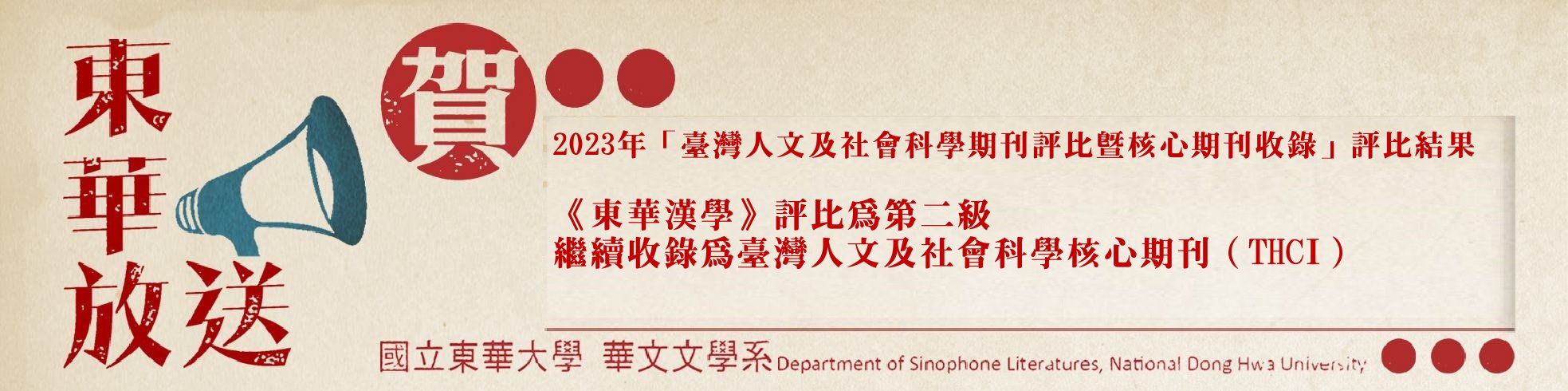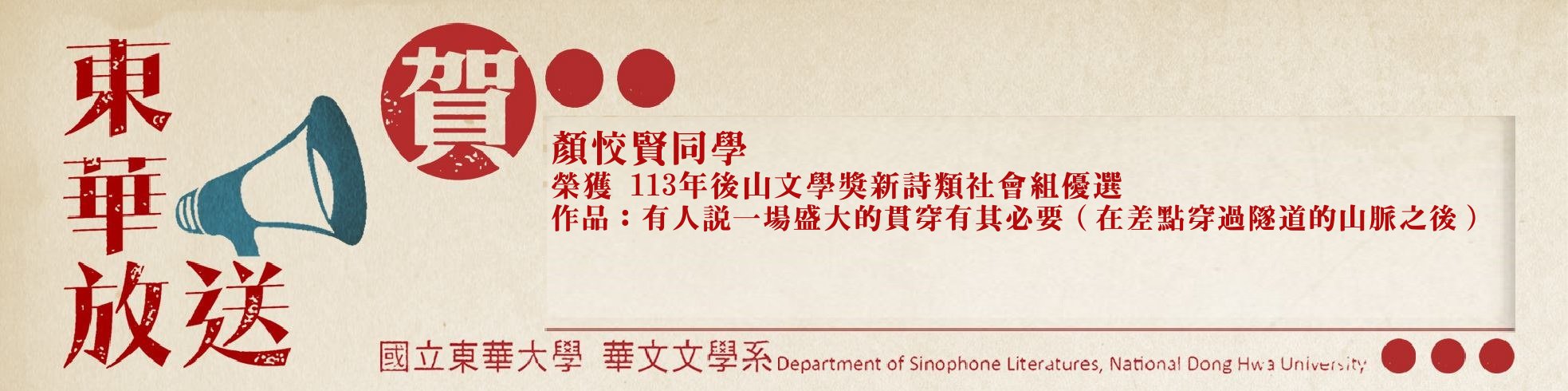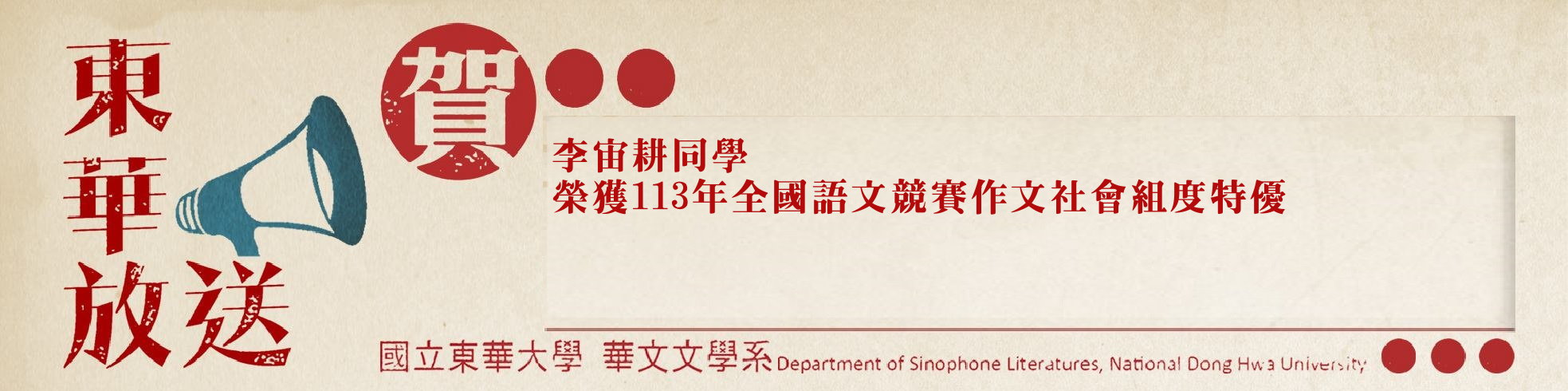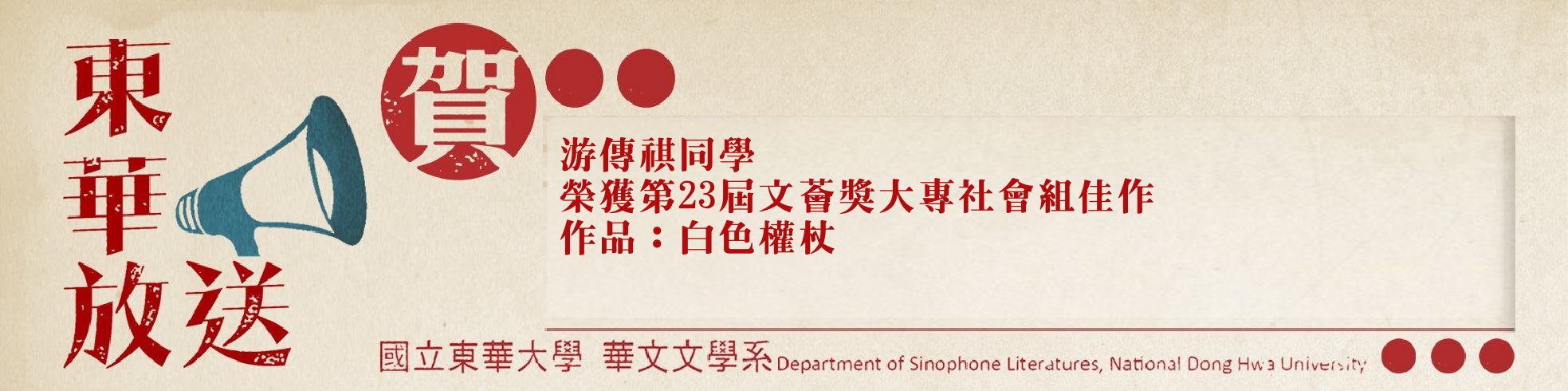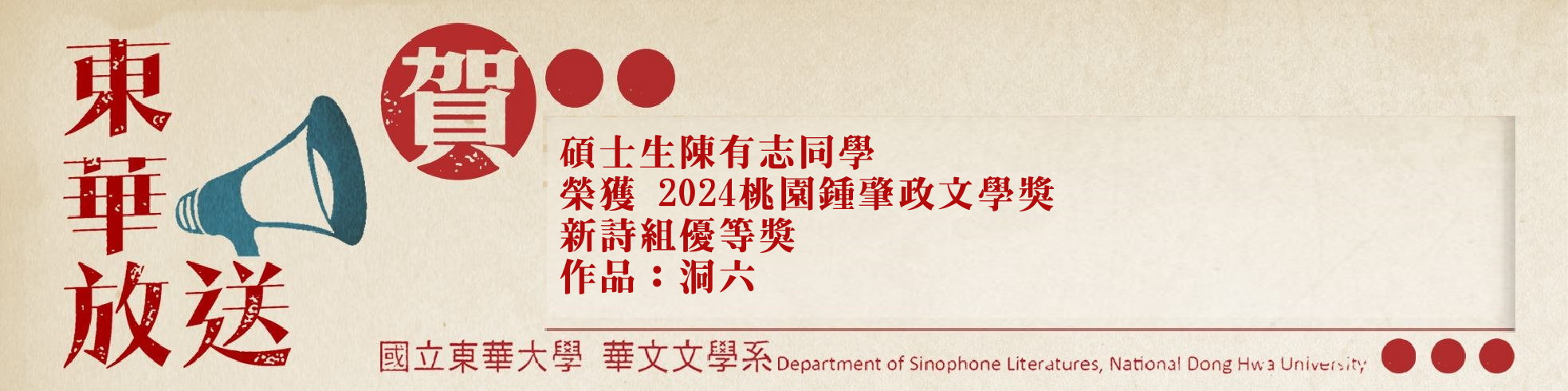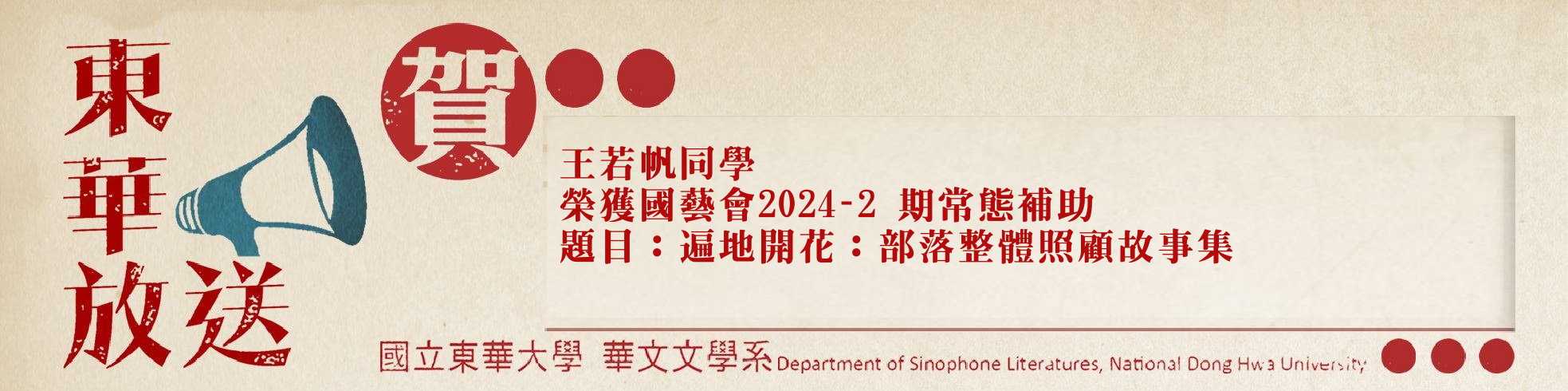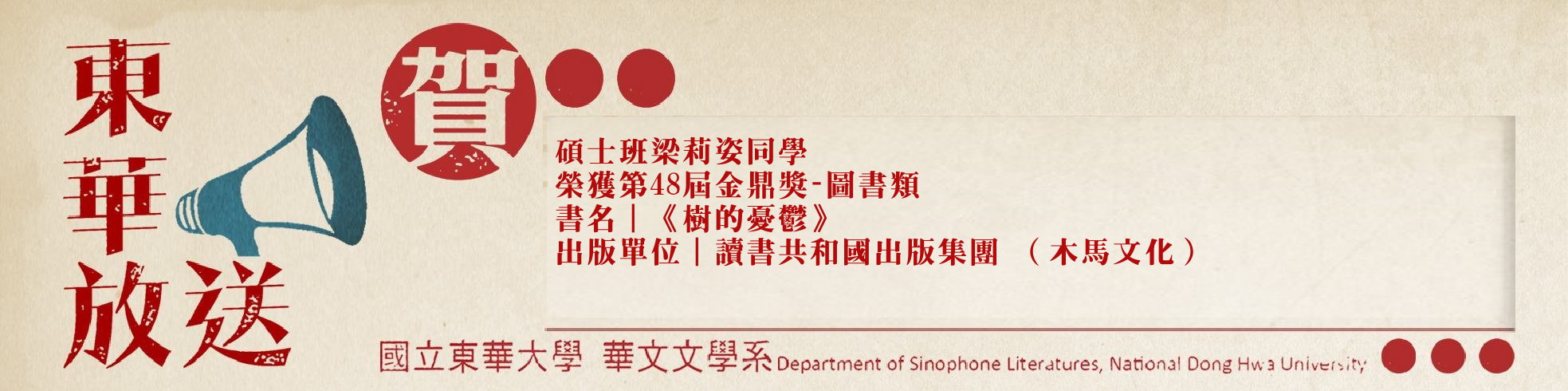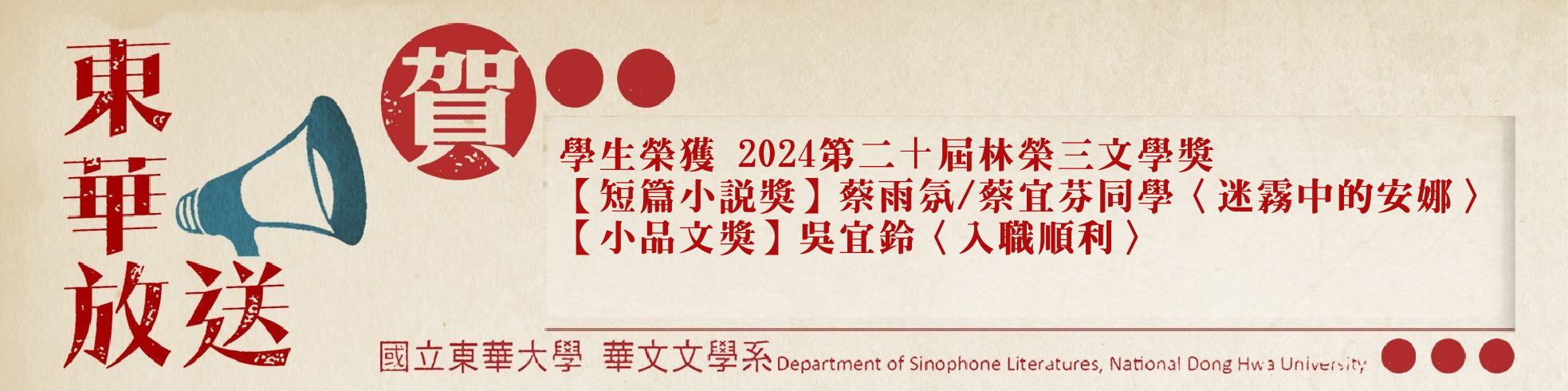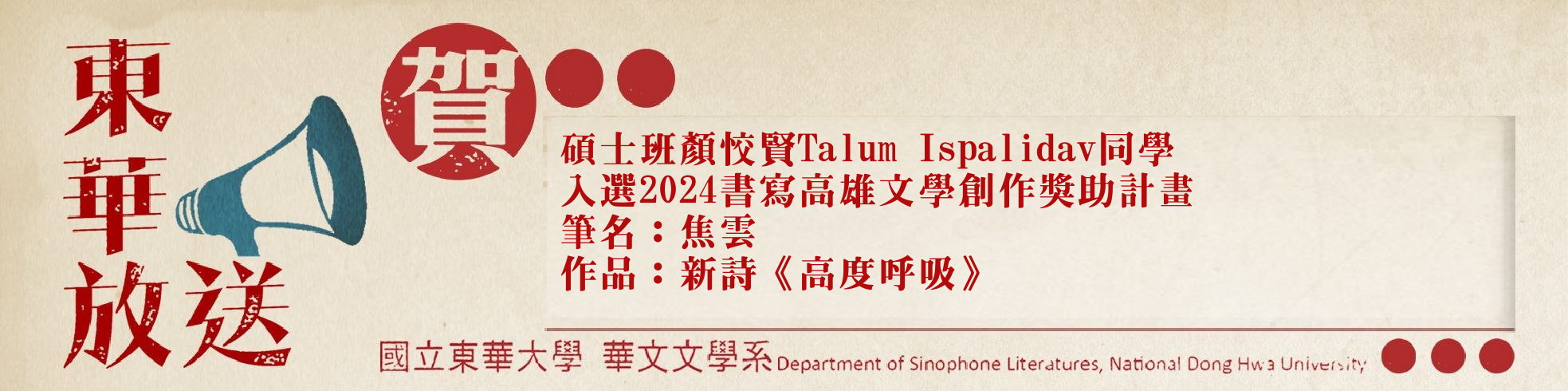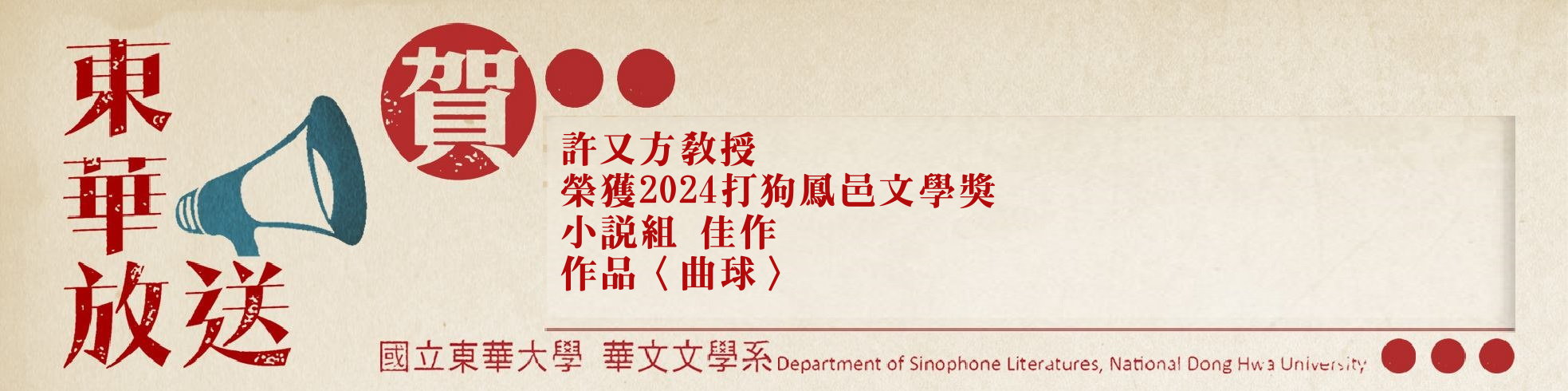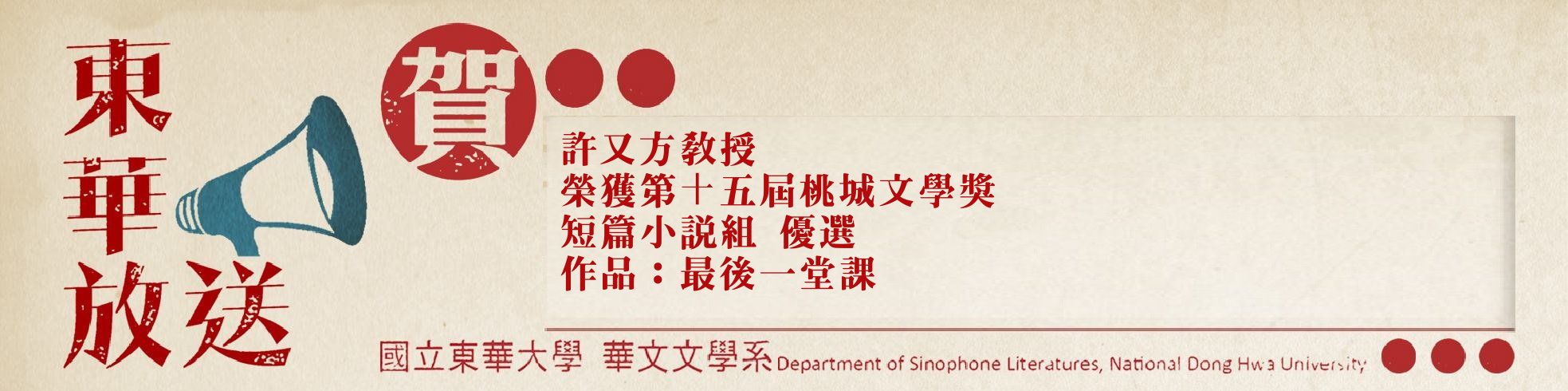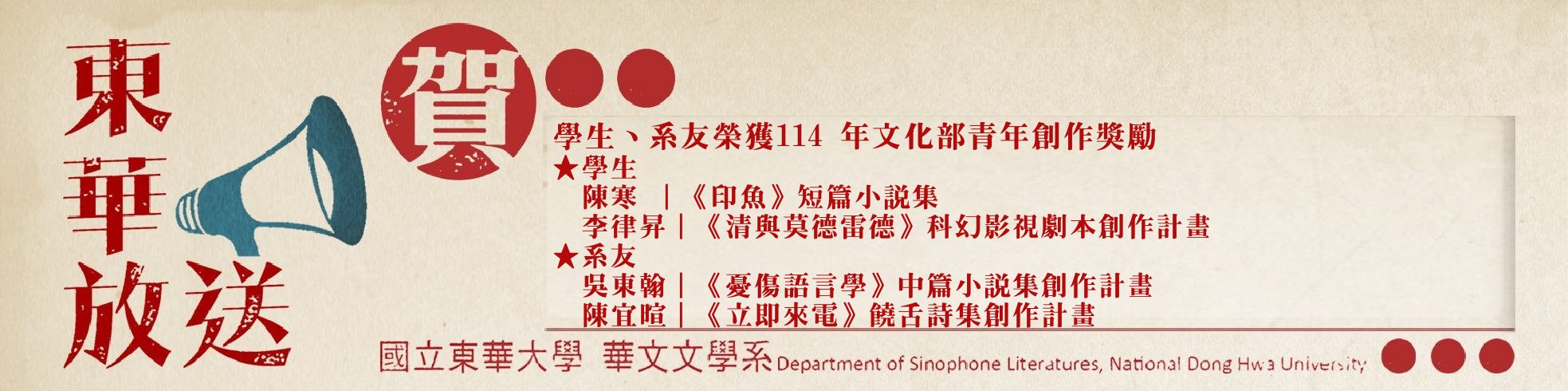演講心得【陳智德老師】∣ 地文與人文:地誌書寫反思
主講人∣陳智德老師
講題∣地文與人文:地誌書寫反思
主持人∣ 劉秀美老師
日期∣ 2022.05.10
地點∣ Google Meet 線上演講
【演講心得∣鄭雯玲】
對於曾經或現在所居的地方,人們若心生對土地的認同,便開始書寫地誌,誰都可以寫,但報章媒體或觀光客的眼睛總是獵奇式的,狩獵著景點與美食。作為一個作家,必須寫出一地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講者陳智德先生引地理學家Edward Relph所言:「『地方感』是人類與世界連結的先天能力。」並表示:「『地方感』呈現也反思人與所在的地空間的關係」,其中的反思之處,正正是使得地誌文學獨立的方式,地誌並非一閉鎖於自身居處地景的文類,而是可進而將地方與地方相互連結的以擴增讀者視野,並具有多重層次。
在地誌書寫中可用三重視野來看待一個地方:「現實的地景」:地方現象、風景、民俗;「觀念的地景」:思想、情感、想像;「人文的地景」:文藝經驗、歷史、蹤跡。講者陳智德先生舉楊牧詩作〈瓶中稿〉為例做文本分析,楊牧於西雅圖時作此詩,詩中的「現實的地景」是位於西雅圖所見的波浪、「觀念的地景」是回憶中的花蓮,而「人文的地景」則是作為每一片海浪起點的花蓮;異鄉西雅圖和家鄉花蓮在楊牧詩作中交互疊合的文藝地景,化為陳智德先生所說的:「一個人文景觀視野中的花蓮」。
對於自己的書寫香港的地誌《地文誌》,是陳智德先生思忖香港被定位為「金融都市」後所欠缺的人文視野的回應,為了「重拾香港人文歷史」,並採以長篇散文的形式作,他認為香港的散文可以承載更多對文化的反思,而不僅限於過往都是「抒情小品」、「雜文」的短篇幅印象。陳智德先生在書中前記說明這樣的長篇地誌書寫是「追跡地方性的文學故事,建構基於本土文化認同的情志和關懷⋯⋯用現有的術語來說,或可歸入一種「地誌書寫」但應該不完全等同,我姑且稱為一種『地文誌體』。」陳智德先生企圖不僅企圖開創散文新貌,更是力圖在文類上有所突破。他所書寫的「地文誌體」雜揉個人或集體經驗以及地理時光的變化,「因此,《地文誌》首先關注他人的文學聲音,文章中我多數最先談論他人的作品,而我的角度,自己的詩當然也有,但全都放到很後,個人化的聲音都是延後的。」這種延後的個人聲音在敘述前人作品時,已夾帶自我的評論眼光和抒情,這種延後不僅是現實地貌時間的延後,似乎也有意將自己放在文學歷史時間之後的意圖。這樣的寫作手法或可扣合前述之三重視野的結合:以「現實地景」為背景,抒發「觀念地景」,最終扣合成自我的「人文地景」。
陳智德先生實踐此種書寫方式基本上有三:「排除習套」:不寫已經被寫爛的地景,比如東方之珠、香港常見之購物中心;「離開中心」:力除政府樣板式的宣傳聲音和描述、已成俗套的地標風景美食推薦;「提防懷舊」:並非是不可懷舊,而是需要謹慎區分懷的舊是過度美化的?消費性的?集體懷舊抑或個人懷舊?
講者以己文〈維園可以竄改的虛實〉為例,書寫高士威道的維多利亞女皇銅像和九龍城的宋皇臺,兩者背後的象徵意義都已隨時間改變,「對九十年代的香港人來說,它只象徵歷史論述的匱乏和斷裂」,人們或許對此二歷史物件無感,但陳智德先生仍有作家自身的立場,因為物件的存在仍有自身的意義,藉此說明自己對文學態度的持守以及力圖還原史實的意念,是為:「尊重歷史,還以歷史本相,引導省思而非訴諸情緒或意識形態」。
這一切實踐,是為以實踐「反遺忘」,陳智德先生強調地誌書寫是「從地方折射出土地、歷史、人文、個人」,因為「土地是寬廣的,寫土地的文學也應如此」,「寬廣的文學造就地文與人文的會通。」陳智德先生以長篇散文式的《地文誌》重新開闊了地誌書寫的範疇,並且展示了文學可以達至的可能性。
【演講心得∣向美英】
演講的開頭,陳智德老師拋出一個疑問,「地方採訪的角度是報導的型態,和文學的創作會有所差別,那文學角度的視野會是什麼呢?地方書寫與文學間應該有著什麼樣的思考?」在文學之中,個人與集體的歷史記憶產生了連結彼此的紐帶,地方作為背景或思想載體,將可見與不可見的地方的現實與想像呈現出來,而文學的作用就在於如何把不可見的東西寫進來,引發反思聯想和行動。
地誌書寫簡單來說就是對某個地方的書寫活動,文學的參與就是將真實地貌透過符號描寫出來,得到屬於作者自身的意義。當我們進行地誌書寫的時刻,我們必須先辨別自我的身分,是在地人?遊客?研究者還是作家?書寫的視角要考慮自己的身分,每個身分可能都有視角上的缺失,像是在地人的地誌寫作缺少他人的眼光,有時候也需要一些有距離的凝視。
全球化與現代化對地方的侵害廣大且深遠,無地方性成為地方的一大問題,地方的特色被掩蓋了,連帶地誌書寫也容易變質,設置成為獵奇的旅遊指南。我們應警惕著全球化,保守和排外的想法也值得我們省思。
陳智德老師為我們朗誦楊牧老師的〈瓶中稿〉,這首詩成就了花蓮的人文景觀,老師提出地景在人文關懷中的三個層次,包含描述地方現象的「現實的地景」、關於懷鄉、鄉愁與母土的象徵的「觀念的地景」以及文藝生命的源頭「人文的地景」。我們可以從創作中觀看作家人生的經驗,也能看出作家對這個地方的感情與反思。老師提到關於地文誌體的態度與地文誌體的形成,是散文結合詩歌、地方寫作和個人經驗的複合體,是複數的經驗和地理時光。
喜歡老師所提「地方之愛」的概念,令人十分感動。寫作時,將地方人物化並不是一種修辭手法,而是作者投入地方情感當中,人地合一的自然流露,像是一種神秘經驗的投入,「地方」有著它自己的感情,能感動人的地誌書寫,即是作者自身被「地方」的感情所深深觸動。呼應到前面楊牧老師的〈瓶中稿〉,流露著對花蓮的懷鄉情感,楊牧老師發現花蓮它自己有深刻的感情,詩中「此岸。但知每一片波浪/都從花蓮開始——那時/也曾驚問過遠方」即是人地合一的成功經驗。
地方的感情比人的感情更深更高,而文學作者的工作就是把地方的感情重新活現在文字上,呈現一個獨立的景觀與視角,把地方的高度與深沉重現出來,把人們的遺忘再現出來,地方的歷史姿態等待我們去挖掘。
老師最後提醒著我們,不要為了迎合他人而寫,要有一個寬廣的角度,因為土地是寬廣的,文學也是寬廣的,持有寬廣的概念與態度看待地方,才能造就地文與人文的會通。
講題∣地文與人文:地誌書寫反思
主持人∣ 劉秀美老師
日期∣ 2022.05.10
地點∣ Google Meet 線上演講
【演講心得∣鄭雯玲】
對於曾經或現在所居的地方,人們若心生對土地的認同,便開始書寫地誌,誰都可以寫,但報章媒體或觀光客的眼睛總是獵奇式的,狩獵著景點與美食。作為一個作家,必須寫出一地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講者陳智德先生引地理學家Edward Relph所言:「『地方感』是人類與世界連結的先天能力。」並表示:「『地方感』呈現也反思人與所在的地空間的關係」,其中的反思之處,正正是使得地誌文學獨立的方式,地誌並非一閉鎖於自身居處地景的文類,而是可進而將地方與地方相互連結的以擴增讀者視野,並具有多重層次。
在地誌書寫中可用三重視野來看待一個地方:「現實的地景」:地方現象、風景、民俗;「觀念的地景」:思想、情感、想像;「人文的地景」:文藝經驗、歷史、蹤跡。講者陳智德先生舉楊牧詩作〈瓶中稿〉為例做文本分析,楊牧於西雅圖時作此詩,詩中的「現實的地景」是位於西雅圖所見的波浪、「觀念的地景」是回憶中的花蓮,而「人文的地景」則是作為每一片海浪起點的花蓮;異鄉西雅圖和家鄉花蓮在楊牧詩作中交互疊合的文藝地景,化為陳智德先生所說的:「一個人文景觀視野中的花蓮」。
對於自己的書寫香港的地誌《地文誌》,是陳智德先生思忖香港被定位為「金融都市」後所欠缺的人文視野的回應,為了「重拾香港人文歷史」,並採以長篇散文的形式作,他認為香港的散文可以承載更多對文化的反思,而不僅限於過往都是「抒情小品」、「雜文」的短篇幅印象。陳智德先生在書中前記說明這樣的長篇地誌書寫是「追跡地方性的文學故事,建構基於本土文化認同的情志和關懷⋯⋯用現有的術語來說,或可歸入一種「地誌書寫」但應該不完全等同,我姑且稱為一種『地文誌體』。」陳智德先生企圖不僅企圖開創散文新貌,更是力圖在文類上有所突破。他所書寫的「地文誌體」雜揉個人或集體經驗以及地理時光的變化,「因此,《地文誌》首先關注他人的文學聲音,文章中我多數最先談論他人的作品,而我的角度,自己的詩當然也有,但全都放到很後,個人化的聲音都是延後的。」這種延後的個人聲音在敘述前人作品時,已夾帶自我的評論眼光和抒情,這種延後不僅是現實地貌時間的延後,似乎也有意將自己放在文學歷史時間之後的意圖。這樣的寫作手法或可扣合前述之三重視野的結合:以「現實地景」為背景,抒發「觀念地景」,最終扣合成自我的「人文地景」。
陳智德先生實踐此種書寫方式基本上有三:「排除習套」:不寫已經被寫爛的地景,比如東方之珠、香港常見之購物中心;「離開中心」:力除政府樣板式的宣傳聲音和描述、已成俗套的地標風景美食推薦;「提防懷舊」:並非是不可懷舊,而是需要謹慎區分懷的舊是過度美化的?消費性的?集體懷舊抑或個人懷舊?
講者以己文〈維園可以竄改的虛實〉為例,書寫高士威道的維多利亞女皇銅像和九龍城的宋皇臺,兩者背後的象徵意義都已隨時間改變,「對九十年代的香港人來說,它只象徵歷史論述的匱乏和斷裂」,人們或許對此二歷史物件無感,但陳智德先生仍有作家自身的立場,因為物件的存在仍有自身的意義,藉此說明自己對文學態度的持守以及力圖還原史實的意念,是為:「尊重歷史,還以歷史本相,引導省思而非訴諸情緒或意識形態」。
這一切實踐,是為以實踐「反遺忘」,陳智德先生強調地誌書寫是「從地方折射出土地、歷史、人文、個人」,因為「土地是寬廣的,寫土地的文學也應如此」,「寬廣的文學造就地文與人文的會通。」陳智德先生以長篇散文式的《地文誌》重新開闊了地誌書寫的範疇,並且展示了文學可以達至的可能性。
【演講心得∣向美英】
演講的開頭,陳智德老師拋出一個疑問,「地方採訪的角度是報導的型態,和文學的創作會有所差別,那文學角度的視野會是什麼呢?地方書寫與文學間應該有著什麼樣的思考?」在文學之中,個人與集體的歷史記憶產生了連結彼此的紐帶,地方作為背景或思想載體,將可見與不可見的地方的現實與想像呈現出來,而文學的作用就在於如何把不可見的東西寫進來,引發反思聯想和行動。
地誌書寫簡單來說就是對某個地方的書寫活動,文學的參與就是將真實地貌透過符號描寫出來,得到屬於作者自身的意義。當我們進行地誌書寫的時刻,我們必須先辨別自我的身分,是在地人?遊客?研究者還是作家?書寫的視角要考慮自己的身分,每個身分可能都有視角上的缺失,像是在地人的地誌寫作缺少他人的眼光,有時候也需要一些有距離的凝視。
全球化與現代化對地方的侵害廣大且深遠,無地方性成為地方的一大問題,地方的特色被掩蓋了,連帶地誌書寫也容易變質,設置成為獵奇的旅遊指南。我們應警惕著全球化,保守和排外的想法也值得我們省思。
陳智德老師為我們朗誦楊牧老師的〈瓶中稿〉,這首詩成就了花蓮的人文景觀,老師提出地景在人文關懷中的三個層次,包含描述地方現象的「現實的地景」、關於懷鄉、鄉愁與母土的象徵的「觀念的地景」以及文藝生命的源頭「人文的地景」。我們可以從創作中觀看作家人生的經驗,也能看出作家對這個地方的感情與反思。老師提到關於地文誌體的態度與地文誌體的形成,是散文結合詩歌、地方寫作和個人經驗的複合體,是複數的經驗和地理時光。
喜歡老師所提「地方之愛」的概念,令人十分感動。寫作時,將地方人物化並不是一種修辭手法,而是作者投入地方情感當中,人地合一的自然流露,像是一種神秘經驗的投入,「地方」有著它自己的感情,能感動人的地誌書寫,即是作者自身被「地方」的感情所深深觸動。呼應到前面楊牧老師的〈瓶中稿〉,流露著對花蓮的懷鄉情感,楊牧老師發現花蓮它自己有深刻的感情,詩中「此岸。但知每一片波浪/都從花蓮開始——那時/也曾驚問過遠方」即是人地合一的成功經驗。
地方的感情比人的感情更深更高,而文學作者的工作就是把地方的感情重新活現在文字上,呈現一個獨立的景觀與視角,把地方的高度與深沉重現出來,把人們的遺忘再現出來,地方的歷史姿態等待我們去挖掘。
老師最後提醒著我們,不要為了迎合他人而寫,要有一個寬廣的角度,因為土地是寬廣的,文學也是寬廣的,持有寬廣的概念與態度看待地方,才能造就地文與人文的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