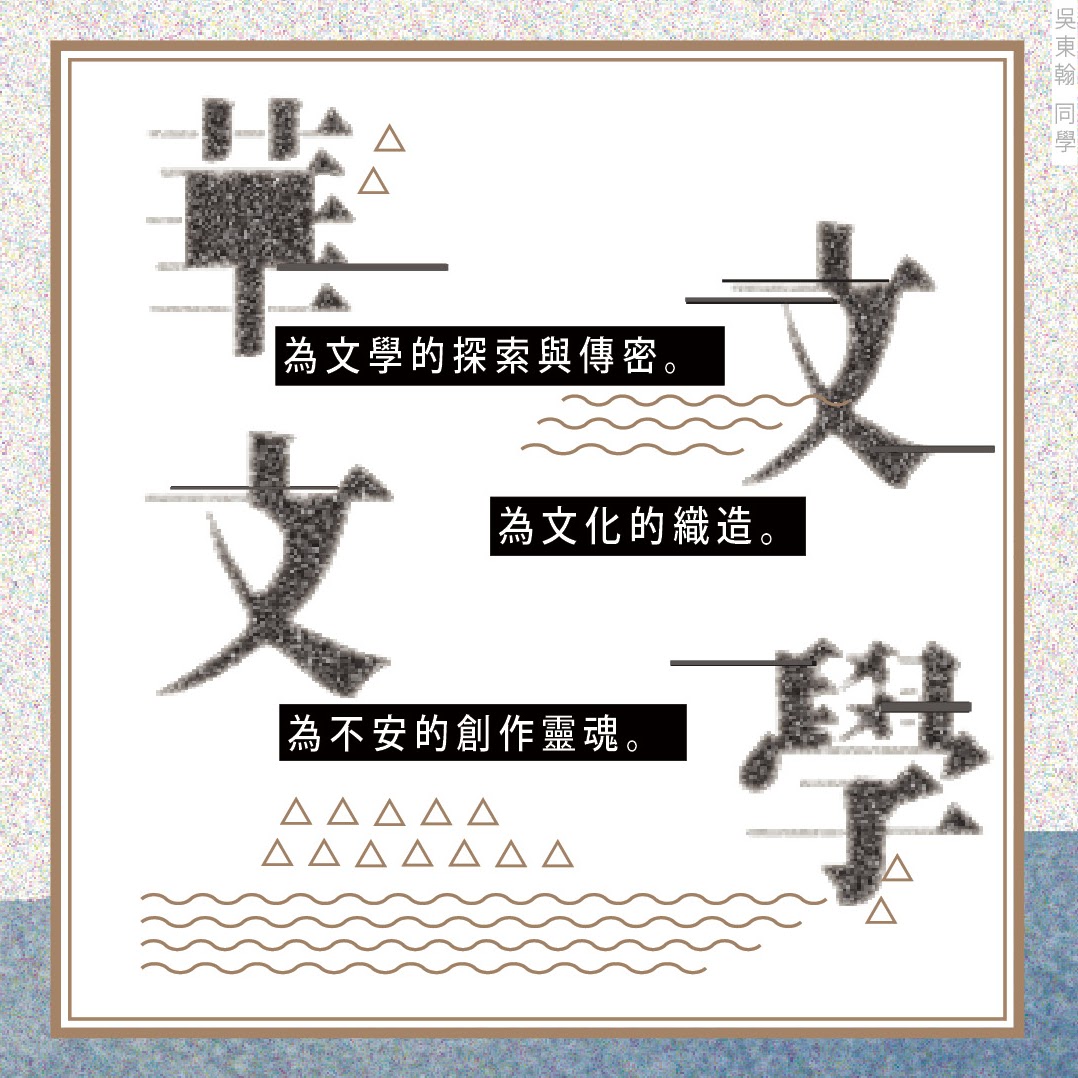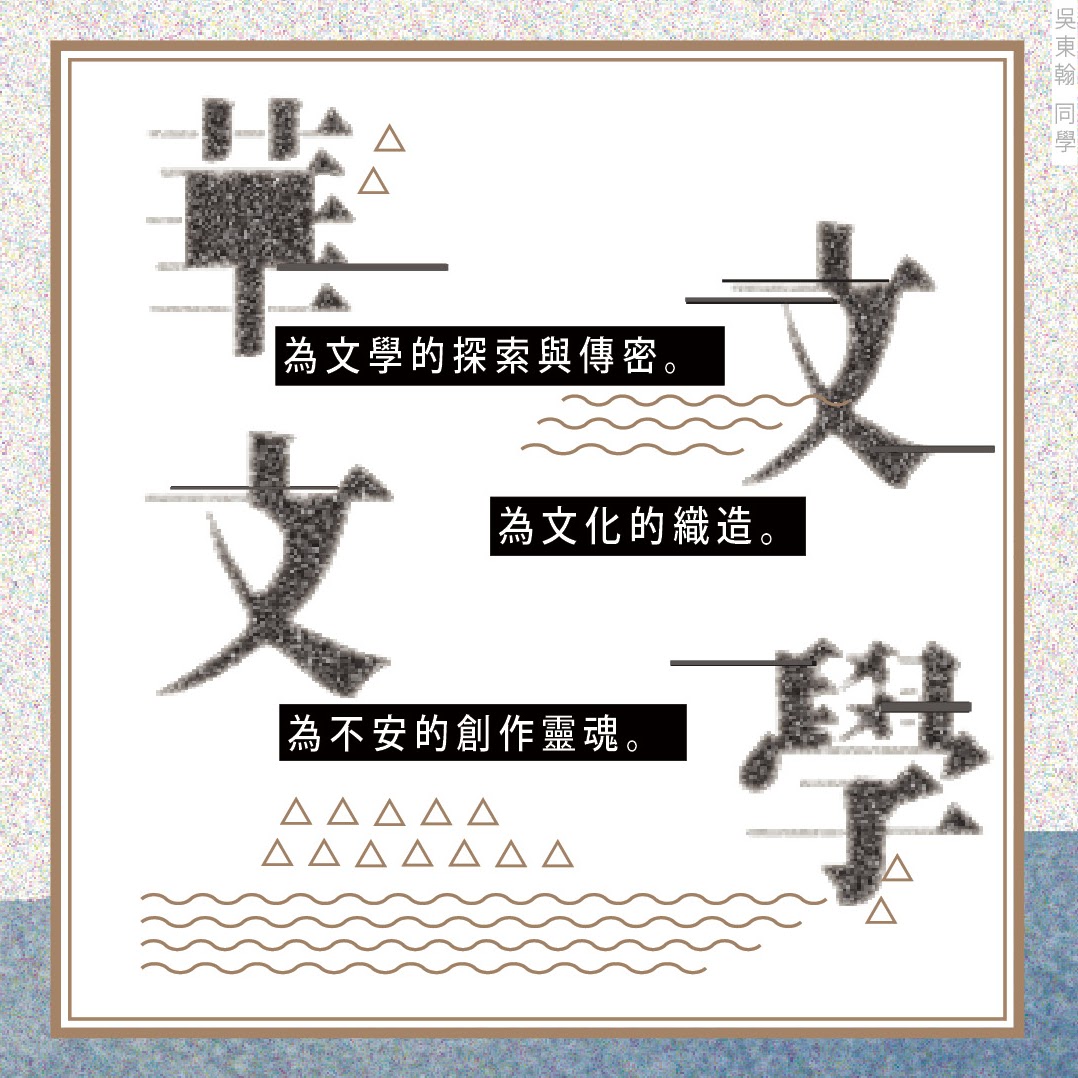主講人∣ 張亦絢老師
講題∣ 論文學、絕望與人生
主持人∣ 張寶云老師
日期∣ 2025.12.05
地點∣ 人一A207會議室
【演講紀錄∣彭以恩】
一、講者人生簡述
講者重視隱私、不喜談論自己,習慣將自己保留給少數人,連星座都不洩漏,對網路上關於自己的錯誤訊息不加以更正,不細心保留過往生命。
大都市還是偏鄉更能培養好的藝術家?講者說自己的故鄉木柵其實很像偏鄉,到公館就像進城,去北投就像出國,木柵人會被看不起。講者自我認同不一定是臺北人,但一定是木柵人。
創作不是為了文學獎,文學獎是讓作品被看見的少數途徑。進入文壇不一定要靠關係。講者投文學獎的運氣很好,與文學的關係「比和諧還和諧」。是否拿獎與作品好壞及作者影響力無關。講者總是才剛失敗,一轉身就寫出一個新東西,列很多寫作計畫,每個都試,這個不成,馬上就換下一個;寫作本身就很快樂,連發表都懶。講者不容易在文學創作上感到挫折,寫作結果往往比預期更好,講者自認真幸福,跟文學的關係是「有恩報恩」。
講者自認閱讀沒有目的,讀什麼就吸收什麼,不帶批判性。講者連洗澡、穿襪子都要看書,不希望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十七歲之前是傳統才女,之後因參與社會運動而變得較不傳統。
二、如何以文學處理「絕望」
講者去巴黎留學時很絕望。原本想在雷恩市考進電影系,卻被電影系負責人在課堂上性騷擾,斷絕電影之路。只有絕望者才寫作?作家都愛自殺?講者自主迴避掉許多同輩作家的自殺事件。自殺不是文學的專利。絕望和自殺是文學作家無法復原的職業傷害。有文學才能者很常不被要求或培養生活能力,導致許多作家是生活白癡,但其實沒生活能力的人很難寫出好作品。熱自殺:即刻衝動;冷自殺:長久謀劃;講者兩者都經歷過,三十歲前都在跟自殺搏鬥。只要在人前,一定不會透露自己不好的一面。為了寫虛弱而變得虛弱,很痛苦。
講者在著作中書寫家中性侵及亂倫的倖存者,對家暴和兒童性侵的諸多型態有廣泛瞭解,倖存者間有共通語言,對此卻無能為力。講者對女同志和自殺議題也有深刻認識。講者曾經歷壓倒性的虛無感,絕望來自巨大災難,災難有各種分類。受害者最大的絕望在於無法阻卻不義。
講者帶領眾聽者討論文學對絕望的態度及功效,大多數同學不認同文學應該抵抗絕望、帶來希望、鼓舞士氣,也不排斥在作品中執著於絕望,因讀者能在他人書寫的苦難中得著共鳴與療癒,作家自身也能透過書寫自我療癒,而文學的目標並非改變社會。大多數同學認為文學應表達殘酷真相,而絕望具有洗滌身心的功效。然而,大家對於文學是否應該「攻擊讀者」這點有紛雜不一的看法,引起頗大爭議,最終未有明確結論。
極內向性格的講者無法明白有人從事艱辛的政治工作,同樣別人看自己也是一樣,無法理解為何有人從事文學創作。各人依其能力和願景選擇專屬自己的位置。
最後,主持人張寶云老師為誤讀講者身份背景向其致歉,承認自己僅讀過她的小說作品,未讀過其散文作品。
【演講紀錄∣邱怡茹】
張亦絢出生於臺北木柵,她認為自己與「歷史」的牽動,並非來自臺北的繁華,而是來自故鄉。那是一種「近城非城」的狀態,使得她對地方、時間與人群產生更為細緻而緩慢的感知。地方並不是一種限制,而是形塑作家性情與觀看世界方式重要的基礎和橋梁。
創作本來不是為了文學獎而存在的,然而對於20歲初、尚未進入文學場域的張亦絢而言,文學獎幾乎是唯一可見、可行的途徑。她從高中時期開始投稿副刊、參與文學獎,被老師喚作「才女」,她認為依賴文字的小孩,文學也會有某種補償,因此她說自己與文學是幸福的、「有恩報恩」的關係。她說她不是一個容易在文學路上受挫的人,她會列出許多寫作計畫,計畫失敗就換下一個,不停留在挫折裡,同時她也認為,創作者應該適度保持與外界的互動。
回歸演講主軸,她問:作家纖細、敏感、容易感到絕望的特質是自殺的原因,還是文學本身容易導致自殺?創作是否構成一種無法復原的「職業傷害」?作家的人生與文學是相連,也是分割的,創作者不可能完全脫離現實生活、社會經驗與人際互動,她認為一個不被要求、不被培養、完全不懂人情世故與生活能力的人,是無法真正把小說寫好的。
接著她說明自己繪製的「思考災難到絕望的路徑圖」,她將災難分成幾個面向,分別是:(一)暫時或長期;(二)歸因明確否;(三)受害公認否。當災難無法被命名、無法被歸因、無法被終止時,絕望便會逐漸生成,身分也在「詮釋人」、「歷史人」、「權益人」、「受害人」等不同身分切換。人們面對絕望時會採取不同方式,有些人透過運動或肉體上的疼痛來削弱心理感受;而文學則扮演另一種角色,她將文學比喻為一種「帳本」,用來計算心理損失,精神破產也與信念的瓦解有關。
「反對絕望」和「迎接絕望」有不同的觀點能切入作品,同時,張亦絢分別以兩部作品舉例說明:
第一種「反對絕望」:「應該要給予受苦者希望,即使看起來不切實際。文學當鼓舞士氣」、「執著於絕望,形同對受苦者的剝削或二度傷害。」、「文學的目標是帶來社會改變。文學即行動,故無所謂絕望。」,作品如包冠涵的《柔軟的耳朵與火山上的歌》。包冠涵早期的作品風格偏向黑色、殘酷且具有高度暴虐性,雖然文采突出,但較難成為「安慰他人」的文本,然而新作轉變了文風,試圖回應與陪伴讀者的痛感,而非僅停留於殘酷的揭示。
第二種「迎接絕望」:「應該要說真話,而真相總是殘酷的。絕望即清醒。」、「如同悲劇的昇華作用,絕望有洗滌身心的功能。」、「不誇大就無以表達。(巴塔耶)」、「文學應該『想像最壞,預備最好』。」、「應該攻擊讀者。」,作品如市川沙央的《傴僂》,透過身障者的角度進行書寫,「像普通女人一樣懷孕並墮胎,是我的夢想。」內容成功冒犯讀者、引起讀者的不適,也引起了爭議。
最後,張亦絢補充道,如果有一天你(創作者)碰到了一個類似絕望的狀況,可以想一想這些絕望裡面還是有很多其他的可能,儘管拉回去跟社會合作也都可能失敗,但一個絕望的剖面,可以讓災難不進入遺忘,或者取消,全力地描寫絕望,或者讓絕望說話,仍然有更重要的價值。不過她也提到,沒有人就沒有文學,所以人還是要活到最低限度,那個限度就是還能寫作,這件事是能互相學習和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