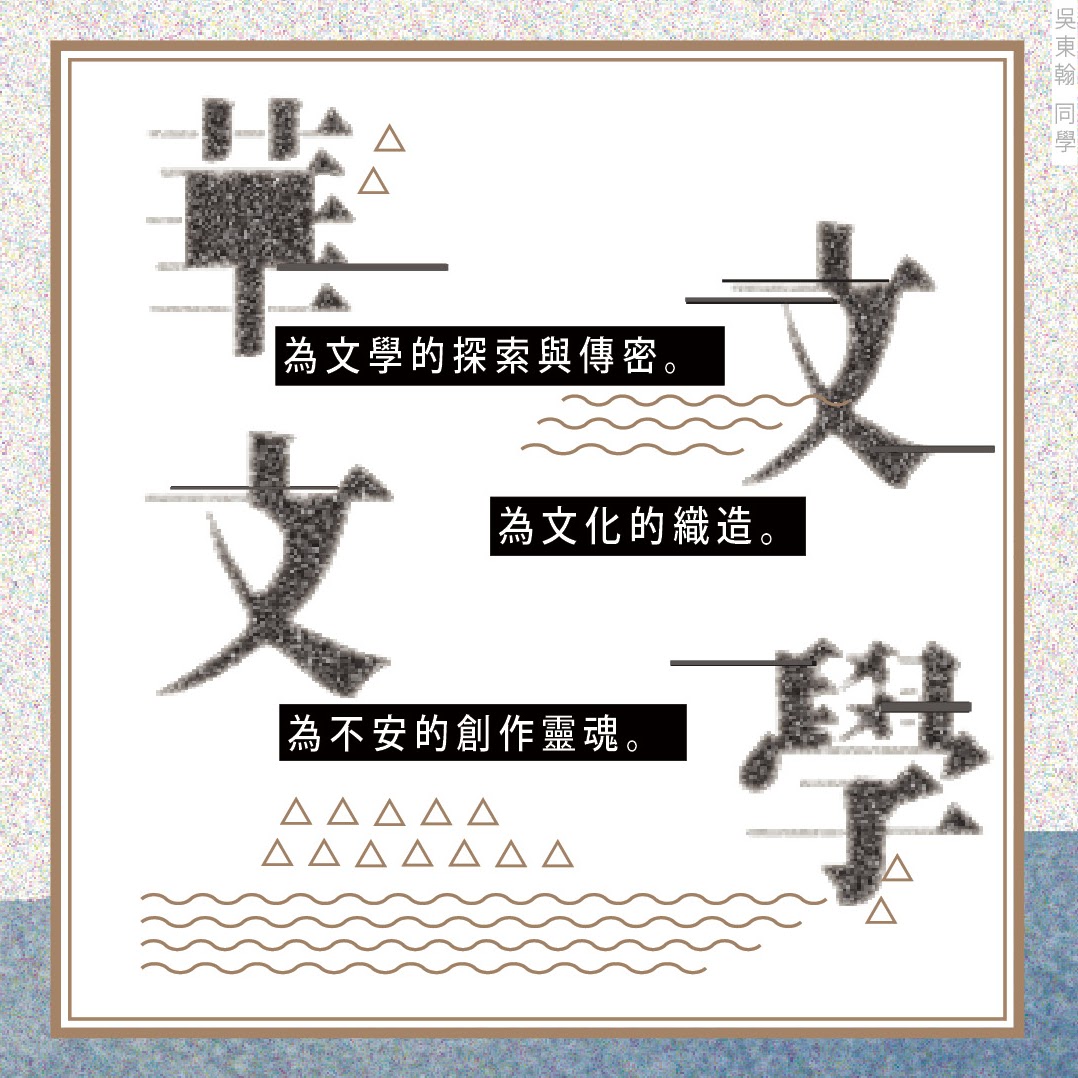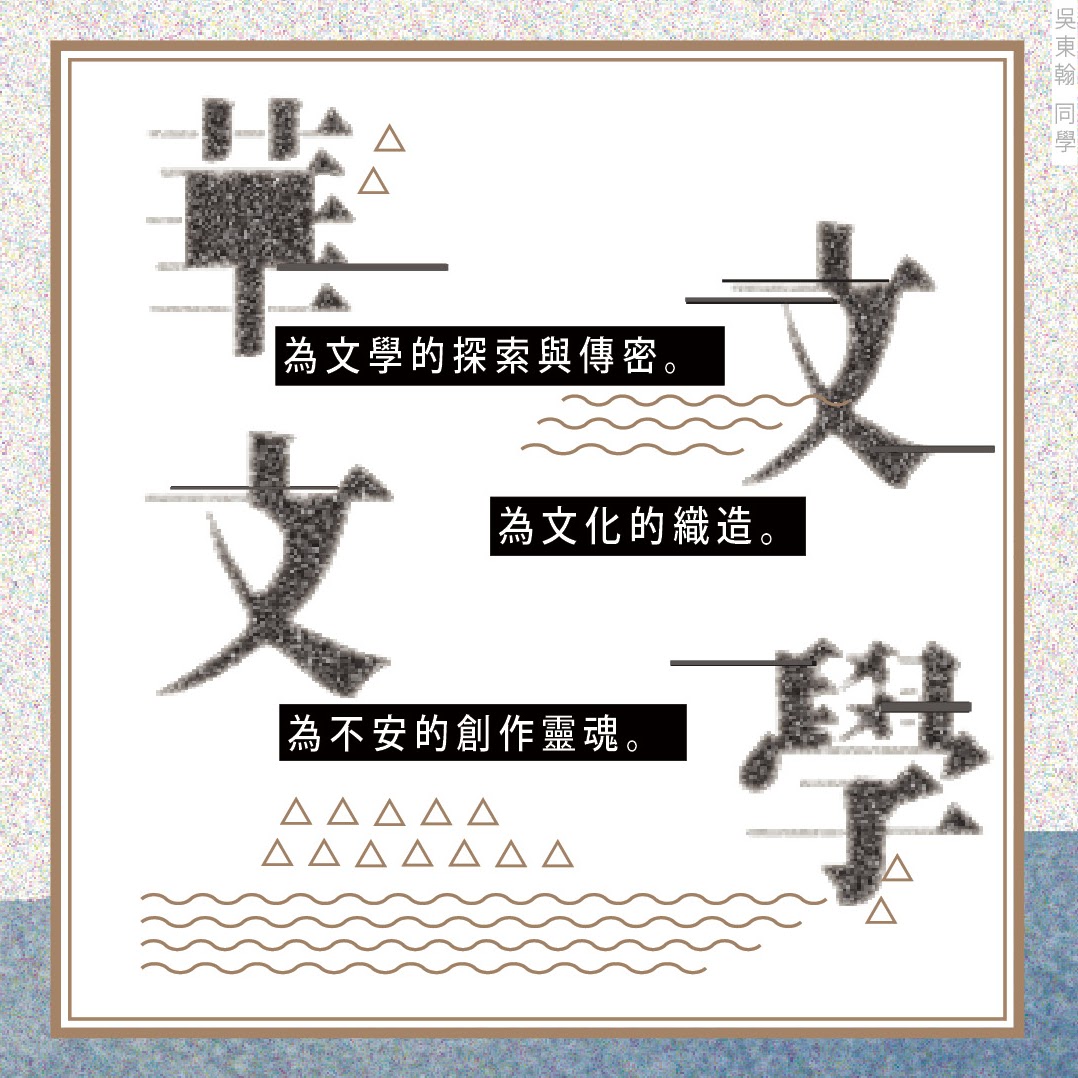主講人∣ 騷夏老師
講題∣ 性的詩啟蒙,詩的性啟蒙:唯物與唯心寫作策略
主持人∣ 張寶云老師
日期∣ 2024.12.12 10:00 - 12:00
地點∣ 東華大學 人社二館 第五講堂
【演講心得∣陳有志】
在本次演講的前半部分,騷夏老師首先分享了她大學畢業後去到時報周刊工作的經驗,在媒體蓬勃發展的時期負責採訪各宮廟的「神祇人員」,而逐漸培養起自己「聊天」的興趣與能力。騷夏老師認為「寫作」對她來說其實就是「溝通」,至於工作則是「窺探人間的窗口」,進行採訪工作的她時常會被丟入無法預期的場所裡頭,並與其中不同的人群接觸互動,而慢慢有了「人情練達皆文章」之認知。此一分享讓我很快就連結到高中時期的自己,那時的我曾在親戚所開的搬家公司底下幫忙,去到過不同的家庭,移動不同的大型傢俱,遷動不同的個人物品,當然也碰到了各式各樣的人,見證大家族的興起與小家庭的分裂,情侶的愛戀和分手危機,沙發底下的灰塵和大兒子幼時的圖畫紙片混雜在一起,還有牆壁上兩個女兒原本並駕然後交互超越的身高劃印⋯⋯通過工作的「窗口」,許多情節複雜的故事或豐沛的情感都將清晰的來到眼前,灌溉愚騃的詩心與幼穉的心靈,探究更恰當適宜的溝通表達方式,藉由散文、小說與詩。
在演講的後半部分,騷夏老師談到了她所出版,同時也是華語現代詩史上第一本女同志詩集《瀕危動物》,並引用芮恩.哈齡《呼吸寫作》所言:「所有失敗的作品都缺少了個人風險」,以進一步講述「誠實」為何是一種重要的寫作策略,而讓我開始反思在自己的作品中所出現的「詞藻華麗處」與「修辭堆砌處」,是否也都顯示出了自我逐漸隱遁的跡象,又自己為何會選擇「不誠實」,為何都已提筆寫作了卻不願迎接風險等問題。接著騷夏老師也分享了她過往的創作經驗與思考主題,說明「性別」若不必非男即女而有曖昧解釋的空間,那麼其概念似乎就像是「詩」,因其語言所富含的模糊性、實驗性以及多元性,使得所謂「隱喻」本身若只有一種色彩或一種性別都絕對不會令人滿足。最後騷夏老師依序朗誦了她的〈據實以告〉、〈舊島電話〉還有〈新娘〉,講述在大家庭的飯桌之上所出現的「父親與父親」,其中較年長的父親們會時刻糾正較年輕的父親們,糾正各式各樣的小錯誤並細細傳承父權的育女原則,另講述母親從家鄉帶來的懼怕,以「島」的意象表現母親神秘的身世與她存在的珍貴意義,以「新娘」的意象表現自我對母親的愛戀與她無庸置疑的美麗。
在聽過騷夏老師的演講並閱讀過她的作品之後,我非常佩服她得以融「個人小歷史」於「家族大歷史」之間的創作構想,並又可藏入自己對性別的觀察,探究長久被壓抑的女性思考與性的想望。作為一個正在追索且熱愛原住民文化的創作者,我也時常在練習書寫家族或民族的大歷史,卻往往使其流為一種冰冷的、旁觀的、無關愛的表面記述。而直到現在才逐漸曉得這之間最大的問題,就是自我的小歷史是否能融入其中,且是否能藏入個人對世界的體察,以及對生活、生存與生命的主觀感受,才可進一步創作出有溫度的、切身的、有關愛的文學作品,創作出有關愛的散文、小說與詩。
【演講心得∣劉芳妤】
騷夏的詩集《瀕危動物》是其在研究所時期的畢業作品,而當時出版時的裝幀與印量皆與現在此次出版不同,亦以編輯的身分解析書籍的印量越多,封面的印刷方式可以有比較多的花樣,因為開版需要一定的基本印量,但現今的書籍印量相對幾十年前都低了許多。
在講座途中也詢問若是沒有靈感時會怎麼做,騷夏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問自己問題,列出的問題有關於父母等使人回顧成長過程,家庭對個人的影響,而問題本身便會勾起某些回憶或是傷痛,在詩集《瀕危動物》便有寫到高雄旗津、父親、母親,詩集的編排也如同詞根不斷擴大為一個詞系。
而回到本次講座的主題「性的詩啟蒙」,也是「詩的性啟蒙」,提到性別不必非男即女,有曖昧的解釋空間,概念就像詩,以及身體書寫與下半身書寫,而許多時候沒有注意到身體性,很容易只有上半身書寫。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在討論詩中使用「妳」這個字時,如果是女生對女生的情感,除了在不同媒材之間對詩的想像不同而有詮釋的差異,就翻譯而言,可以知道英文中有可對應「她」的人稱代名詞,但是「妳」並沒有對應,又該如何翻譯,我同時也在思索中文以外是否有語言可以對應這個翻譯問題。
講座中亦提及「誠實」,騷夏認為看到文章中如果作者開始用一些華麗的詞藻,不代表華麗的詞藻不好,很有可能是要隱瞞某些事情,使我也思考了我在創作時的誠實,而誠實的對象是自己,不是別人,我認為我在寫散文時相對於詩,會更需要回到事情發生的現場,凝視著那些過往,並再加以用文字重新敘述一遍,通常我會寫到覺得有些可怕,而可怕源自於書寫散文的過程得要誠實,但是唯有誠實才能推動文字的書寫。
【演講心得∣林儀涵】
騷夏算得上是系上創作所的大學姐,出發演講前一天她還特地翻出自己當年的畢業證書。推算起來,距離學生初寫作的時代已有將近快二十年的時間,至今她仍堅守在這條道路之上。她因此想和大家聊聊自己走過的路,希望能提供給年輕的創作者一些參考的策略方向以及思考寫作生涯的切入點。
畢業之際,就像大多數的學生一樣,她懷著各種不安與困惑踏入職場。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神職人員的採訪記者。雖然這份工作並未做得太久,但她認為「被丟到一個陌生環境,想辦法取得需要的畫面、取得那些想要問的答案」,這樣的歷練補足了她對自我「人情練達即文章」的缺憾。她一直認為在那份工作之前,自己不過是靠著某種學術養分、小聰明在創作。文學場域以外的工作之於她,是一種窺探人間的窗口。
演講中,她像當年從事記者的工作那樣,列出了一整頁 PTT 的訪綱。她請大家訪問自己,題目像是「當您回想您的父親母親,哪些事件會跳出來?」、「如果要您選擇某一動物來象徵您與父親母親的個性,您會選用哪種動物來敘述?」、「如果您的父親母親可以為您做一件事,您會希望是什麼事?」
在討論這些問題前,她先分享了自己的經驗。她的詩集《瀕危動物》是華語現代詩史上第一本女同志詩集,但時間拉回到更早以前,當她剛從大學畢業、拿著自己的作品到研究所面試時,有位主考官仔細看了以後詢問她是不是女同志。在場外陪考等候的父親聽見她轉述問題後,立刻說:「啊你趕快跟老師說你不是啊!」騷夏說,那算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在公共場合出櫃的經驗,於此同時,也是啟蒙的時刻──她認為一個創作者首先要對自己誠實。
上述那些詢問與父親母親有關的問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釐清自己從何而來;而關於自己要從何而去?騷夏認為,誠不誠實對於一名創作者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寫作會有風險,很大的風險,暴露了自己是很危險的事。但她誠實的陷自己於險境之中,這就是她所選擇的寫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