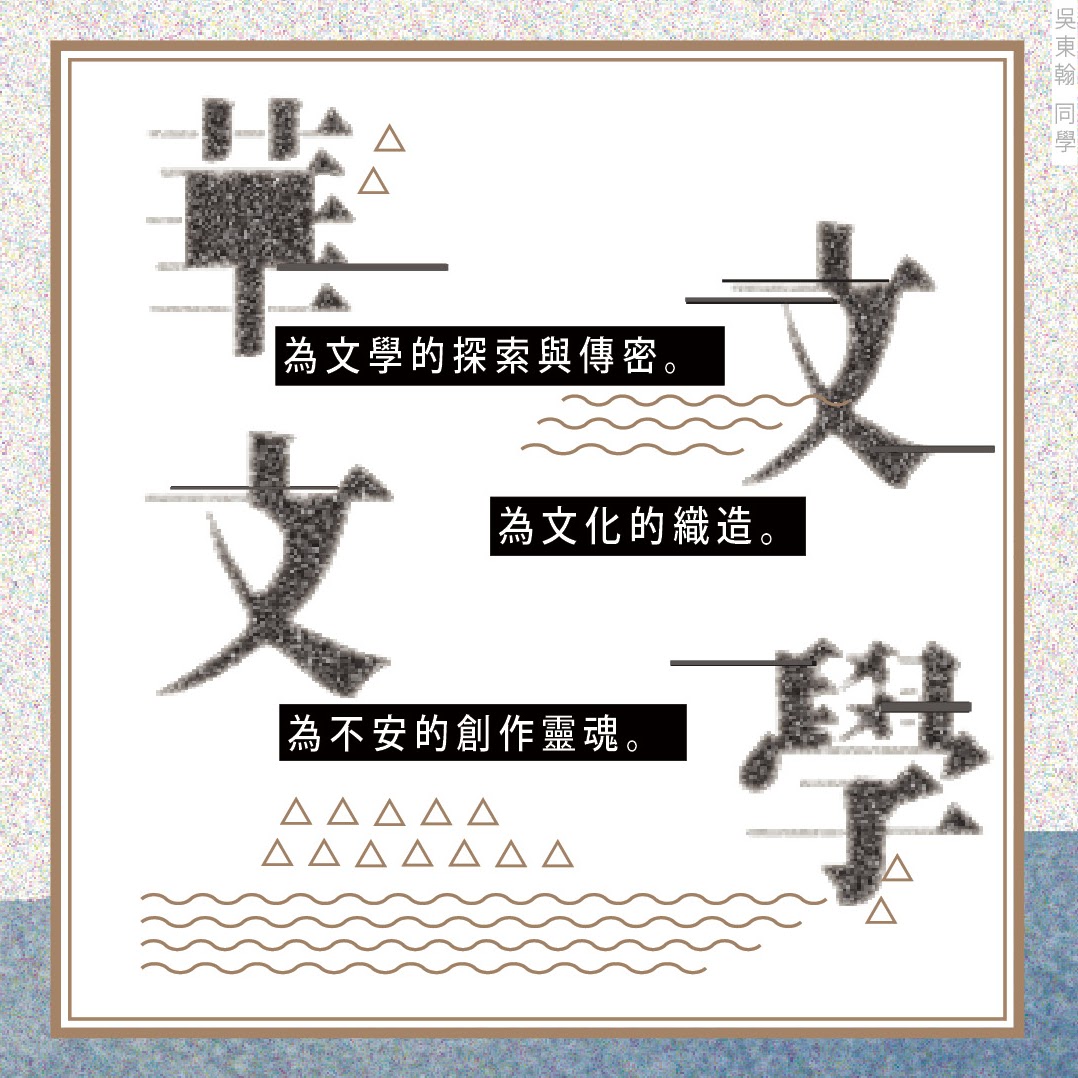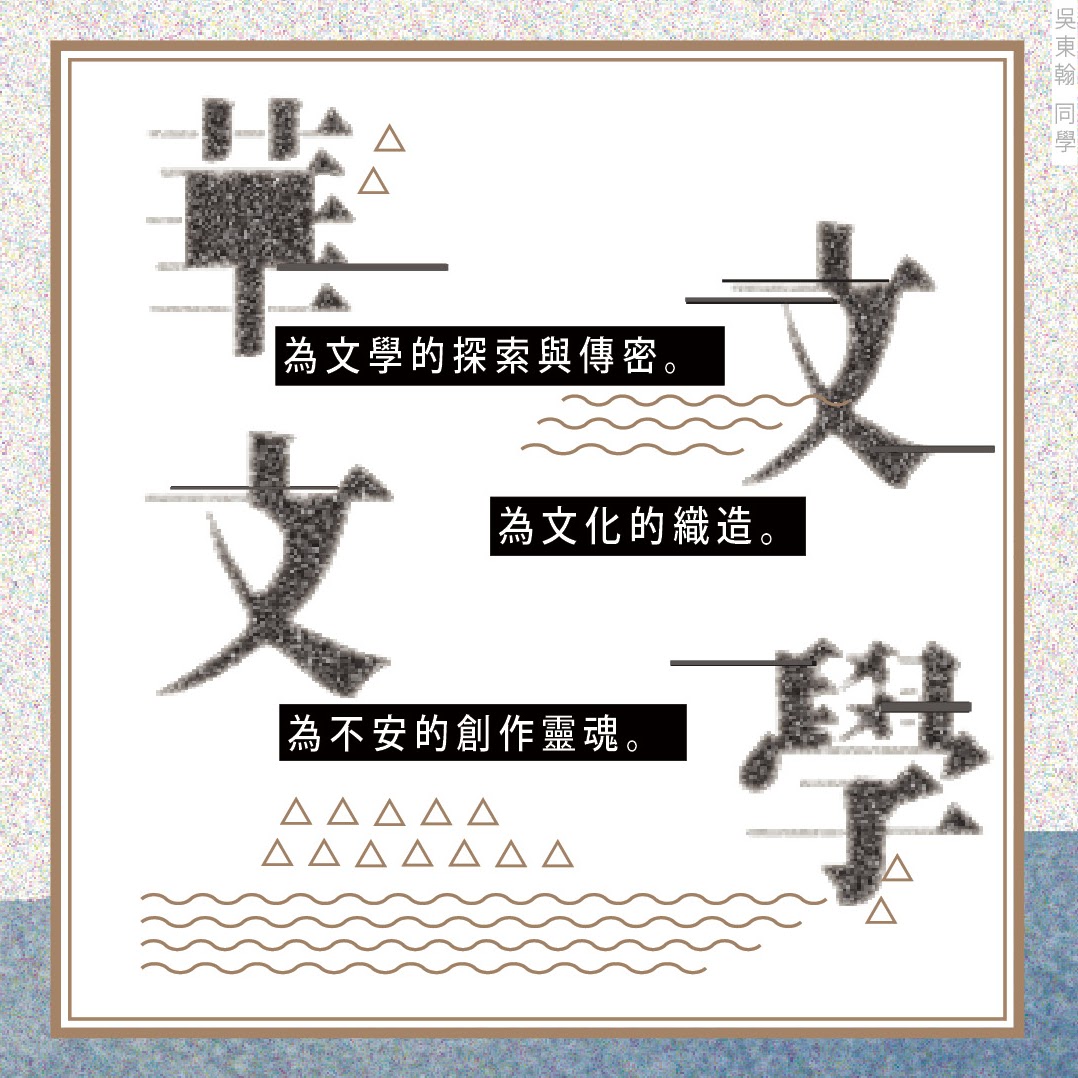主講人∣ 王德威老師
講題∣ 可畏的想像力
主持人∣ 黃宗潔老師
日期∣ 2023.05.17
地點∣ 管理學院第二講堂
【演講紀錄∣許聖傑】
王德威教授首先提到了政治哲學家、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公告生活和說故事。講座主題也將聚焦在「說故事」當中,漢娜鄂蘭認為,「小說」並非僅僅在課堂上能夠出現,亦能在生活的「溝通」之言辭來建立,除了男女之間、家庭之間的溝通,也能提升到教育層面的溝通,都牽涉到敘事者、言聽者,都是說「故事」的一種呈現,因此它是比較廣義的說法。講者提到《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只有那些倖免於肉身凌辱,尚未因種種而成為行屍走肉的人,才得以在見證不義之餘,有能力想像種種恐怖——並運用這可畏的想像力,這樣的想像有助於思辨政治情境,啟動政治情懷。」屠殺的不以為意,現實當中顯示出的緩刑的暴力,是漢娜鄂蘭感到錐心刺骨的情況,也是一種現代性問題,滲透到日常生活裡頭。
漢娜鄂蘭對想像力的定義得自康德「審美判斷力」的啟發,也和業師海德格視詩歌為打破混沌、顯現靈光的說法,有所應和。講者提到,漢娜鄂蘭的想像力強烈訴諸公共層面,「主體」於她不是個人存有,更是人與人「之間」形成的社會關聯性。王德威另外展開了巴赫金「眾聲喧嘩」概念,以及班雅明「說故事人」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性,所謂的「說故事」,不同的社群、不同的聽眾、同樣的故事,卻達到豐富的共感。並且提到了戲劇家哈維爾,在1990年率領捷克人民脫離極權社會,他認為,極權社會如此和諧,以致沒有「故事」可講,甚至摧毀了故事。王德威另外提及了習近平《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一書,和哈維爾的論述有相當微妙的關聯。
什麼是在有效社群裡說好一個故事?講者走進中國文學的語境裡,馮夢龍:「史統散而小說興。」,社會的價值混亂,歷史恐怕不再能夠信任,而現實生活的稗官野史得以流傳。馮夢龍的思想,表現出小說灌注在儒家的道統中,於此同時也解構了傳統。另外,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以「熏、浸、刺、提」作為小說的渲染特點,講者提到,有害於世道人心的文類作為一種翻轉,成為改善民心的文類,小說是有毒的,但它同時也具有某種魅惑力,因此,以新的面向來為我們所用,是為「以毒攻毒」,進而呈現出新的效果,該論述不只是晚清知識份子所提倡的看法。講者引述:「檮杌由怪獸、到魔頭、惡人、史書、小說的轉變,是足以說明中國文明對歷史、暴力、敘事想像的一端。有鑒於歷史中的暴力層出不窮,我們必須尋思:歷史是對怪獸也似的暴力的記錄,或者竟是其體現?我們對歷史與怪獸的開聯,是戒慎恐懼,還是視而不見?」其又回應的漢娜鄂蘭在道德反省、暴力的自身、惡的自身上所提出的種種問題。也正因為歷史的殘暴性,我們才更有必要與其周旋。
當代文化傳媒千變萬化,王德威認為,「小說的影響看似式微,弔詭的是,小說失去了上個世紀文學的焦點位置,文化、政治建制的青睞,反而獲得了空前解放。」或許顯示出一種更多可能的想像。林俊穎《猛暑》(2017)、陳冠中《盛世》(2008)《北京零公里》(2020)都想像出一種現實的「未來」。被小說家改寫的歷史,其中馬家輝《龍頭鳳尾》用不同的方式寫出了香港被佔領的情況,改寫自張愛玲《傾城之戀》(1943)的故事,同時也影射了更多當代歷史的各種變化,王德威認為,裡頭或許具有不可啟齒的政治意圖。而黃錦樹《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2014)、嚴歌苓《陸犯焉識》(2011)也處理到各種歷史政治層面。作家談到種種歷史陰暗面,其中的生存挑戰,王德威認為是中國大陸恐怕難以深入接觸的,陳雪《摩天大樓》(2015)則對人性黑暗面具有非常深刻的描寫。原住民作家夏曼藍波安《大海之眼》(2018):「原來我們的海洋不一樣,我們的海洋沒有國界⋯⋯」王德威認為,夏曼藍波安的國族論述,不應過於簡單的被分類評定,是以他個人航行經驗,解構了故鄉的想像。伊格言《零度分離》(2021)處理到真實的關係之意義,是在當代科技世界的一種想像。
講座結尾,王德威提及關於未來的敘事倫理作結:「歷史經驗千頭萬緒,我們其實無從以先驗或後設方法化約其動因和結果。當此之際,文學以虛構力量揭露理性不可思議的悖反,理想始料末及的虛妄,從而見證歷史俱分進化的現象。這一虛構力量所激發的『幽黯意識』起自個別、異端想像,卻成為文學批判公理世界的重要契機。」
【演講紀錄∣王若帆】
王德威在開場時先給出本次主題「可畏的想像力」,所要討論的是小說或廣義定義的敘事文學,他所存在的功能、他所投射的政治影響力,還有小說作為敘事倫裡的機制,可以帶給我甚麼樣的啟發。
「可畏的想像力」一詞來自20世紀的思想家漢娜‧阿倫特,關心1960年代中,關心當時世界在冷戰格局下的紛紛擾擾,所提出的看法。
漢娜‧阿倫特為出生於德國的猶太裔學者,她在青年時期經歷納粹政權、種族壓迫,以及極權主義間的鬥爭等,對她無論學術生活或私人生活都造成深遠的影響。阿倫特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納粹政權對游的迫害而流亡到美國,在美國這樣殊異於先前所居住的德國的環境中,漢娜‧阿倫特持續思考冷戰前、冷戰間思紛亂的政治局勢,對當時的世界所帶來的影響。
漢娜‧阿倫特提出,「公共生活」和「公共社會」和我們最息息相關的面向,往往是以「說故事」來呈現。
甚麼是故事?一般大家所關懷的「說故事」,或約定俗成的「小說」文類,漢娜‧阿倫特認為公共社會中,需要彼此連結,方能形成溝通,溝通不是打招呼而已,而存在於所有形式的關係中,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不論是原子個人,教育、社會、父母子女之間,或甚至選戰中的政治論述,這些公共論述都是溝通,牽涉到敘事者、聆聽者、傳播者之間起承轉合的論述,這都論述,都是一種「說故事」。
漢娜‧阿倫特認為在任何公共的場域,我們彼此溝通的時候,要「把話說清楚」、要「給一個說法,要說出來龍去脈的敘事,需要這個社會有一個約定俗成的互相了解,而且在約定的過程也必須不斷傳達並辯證彼此的意象,「說故事」也不再只是日常隨意的溝通,而是倫理的承擔、意義由此至彼,由過去到現在乃至於未來的傳遞,所以「說故事」對於漢娜‧阿倫特來說,是一種言說的重要方式。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漢娜‧阿倫特回顧60年代前的歐洲所經歷的各種各樣風暴,她提到各式各樣因政治形成的暴力,亦即暴政,可以以最平庸無感的形式滲透到日常生活裡,我們看見表面的生活如此平靜、和諧、優美,但一旦我們習慣了無孔不入滲進生活中的暴力,我們就會習以為常。如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行為,是當時雅利安人德國公民的習以為常,他們認為猶太人本來就是格格不入的外來者,本來就該清除的一乾二淨,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參與屠殺猶太人的人,對屠殺不以為意,白天的血腥轉化成夜晚家庭的天倫之樂。在最平常的日常生活裡,隱含著如此強烈的暴力,對漢娜‧阿倫特來說,是椎心刺骨的現代性殘暴的演現,而我們對生活中的暴力視而不見、渾然不知,是「現代之惡」最詭譎的形式。
而鍛鍊「可畏的想像力」,便是用以對抗歷史怪獸的無孔不入,這些怪獸在不知不覺間滲透進每個角落的縫隙,只有那些倖免於凌辱,尚未因劫難而成為行屍走肉,尚可保有一些自由餘裕的人,才能在見證不義之餘,有能力想像種種的恐怖。
阿倫特號召,只要我們還有空間和機會,就該運用這種「可畏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有助於思辨政治情境,啟動對政治的激情,來批判或觀察現代社會帶給我們的種種暴力。
阿倫特所定義的想像力強烈訴諸公共層面,如果康德和海德格所強調的審美或倫理是來自於個人主體對於社會的種種交涉反映,阿倫特更強調的是這種政治、社會、倫理、審美的想像力,永遠都是存在社會群體之間,是一個公共的層面,是人與人之間形成的關聯性。
我們如何建立彼此的相關、關聯、關懷,甚至彼此間的批判?阿倫特認為必須要用言說的方式,一旦你出口成章,一旦你落筆為文,或者一旦透過各種傳媒在平台開始發聲,溝通就已經展開了,藉由這廣義的「說故事」,我們相互言說與傾聽,相互交鋒與對話,公民社會的意義就能因此而敞開。
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批評家巴赫金,他最有名的關鍵詞是「眾聲喧嘩」,亦即在一個大的社會歷史交集的層面,各式各樣的聲音彼此交會,形成複雜的對話群體。
班雅明提出「The sotryller」說故事人的觀點,說故事人在人群間走動,用動人的故事,連接不同人群同情共感的社會性,說故事的人不見得有甚麼大學問,但他們有豐富的經歷,見多識廣,在不同聽眾、不同情境裡,同樣的故事會產生心靈交通的震撼感,不同的人對說故事的人都有感同身受的回饋。
劇場演員出身的捷克總統哈維爾,致力於用戲劇形式反抗共產極權主義,在1990年代率領捷克人脫離蘇聯統治,他認為在極權社會裡,統治者希望社會看來社會看來一片和諧、萬眾一心,以至於這樣的社會裡沒有故事,因為所有的故事總是要告訴你有趣的經歷、奇怪的遭遇,不可思議的過去和未來──這些都不是統治者所樂見的,統治者只要民眾聽事先預備好的一種故事,大家有一個基本營養、可以過ㄖ子就行了,不要多講亂七八糟的故事。所有公共傳媒都會將故事性降到最低,導致這個社會如此和諧、如此萬眾一心,以至於沒有故事可以講,大家每天都過得一樣,說著重複的話,這就是一個沒有故事的社會,對哈維爾來說是一個可怕的社會。
中國領導人在習近平在2014年出版「習近平講故事」,其目標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我們會問,這個好究竟是甚麼?他是動詞?形容詞?他是教你叫你好好講,否則就有好戲看了?還是只有忠孝節義的好故事?「講好中國故事」變成了很重要的中國指標。直到之前疫情,習近平也出來要大家講好抗疫故事,也就是萬眾一心的故事。
但我們也要反省,台灣的故事又是怎麼樣呢?裴洛西在2022年說,台灣的故事,就是一群熱愛自由民主人民的故事。台灣人快樂的說故事,但同時背後有飛彈的陰影,說故事是有風險的,說故事有時候也可能是一廂情願的。
因此,我們要反省甚麼是故事?什麼是講好故事?甚麼是在有效的社群環境中傳播故事?
在華語的語境裡,中國學者也對「講故事」有所感悟,如晚明馮夢龍,曾提到「史統散而小說興」,在中國傳統文學的位階中,小說是不入流的,但馮夢龍在一個史統綱常混亂的時代中,他想像小說作為巷議街談、稗官野史,可以形成另一種力量。他認為「史統雖然散,小說能興起來」,他把小說作為在史統散失的時代,可以灌注道統和儒家思想的方法,這是他仍有侷限的地方,但不論如何,他已經開始解構小說,想像成為史統的替代。
晚清時,知識分子梁啟超創辦「新小說」,他呼籲把傳統文類顛倒過來,過去認為詩歌散文重要,梁啟超認為小說才重要。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提到:欲新一國之民,必新一國之小說,他全面出擊式的把小說的位置抬到國家人文論述的最頂端。梁啟超說,小說有各式各樣不可思議的故事,把各種各樣的過去排列組合,發揮不可思議的力量,他便是革命最重要的契機。
梁啟超心理明白在傳統的士大夫文化觀點裡,小說是一個誨淫穢盜的文類,有害世道人心的文類,梁啟超為什麼想用小說來做為拯救中國的媒介?梁啟超了解小說是有毒的,但這種毒如此魅惑、深入人心,我們可以利用小說重新包裝、給予新的刺激,便能改造民心士氣。梁啟超有一種很不同的期許,這便是梁啟超的以毒攻毒論,後來也被選擇性的用來中國對小說的推動。從梁啟超、毛澤東,習近平,都認為可能都是有害的,但我們要好好地用他,用一個有傳染性的東西,讓他們為我們所用(就像打疫苗),推而廣之,「說故事」就成為了他們的方向。
我們再推回來,介紹「檮杌」,這是一個遠古的怪獸,在不同時代皆有不同的形象描述和象徵,到了民國後,從中國逃到台灣的作家姜貴以「今檮杌傳」來回應這個亂世,和共產黨的荼毒。我曾引用這個隱喻,書寫「歷史與怪獸」,我們必須思考:歷史中的暴力層出不窮,歷史是對怪獸也似的暴力的紀錄,或是其體現?我們對歷史與怪獸的關聯,是戒慎恐懼,還是視而不見?
到了二十世紀,這些問題變得更為迫切,所有事情都變得像未來的烏托邦,我們有可能已經成為了一種龐大的,以民主、科學、革命、進步為命的怪獸的一部份了嗎?
我們還會自動自發的看小說嗎?梁啟超在百年前想像小說可以改變人心,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小說現在雖然式微,但說故事的方法千變萬化,這依然是一個說故事的社會,比方選舉前,候選人在競選時講了一個又一個「故事」,就是政壇怪獸在變戲法。
雖然小說失去了文化焦點的位置,反而獲得了空前的解放,在20世界的第20年,小說雖然不再是萬眾注目的文類,但只要大家在未來放下心來,看一兩本我等下推薦的小說,這些故事都無比精彩,作家在文字建構與解構的天地裡,言說那不可言說的,想像那不敢想像的,如此肆無忌憚,卻讓人心有戚戚焉,因為他們證明了,文字作為最古老的傳媒,他的魅力依然無窮無盡。
在民主、自由、進步等各種大說帶來的各種混亂的廢墟間,如何將我們這個世代的故事講下去?我們不只仰賴想像力,而是「可畏的想像力」,不是簡單的故事,而是一些可怕的故事,是理性推演到極致之後,在那些非理性、超理性的幽暗地區,當代小說家發揮了他的潛力。
〈猛暑 林俊穎〉
2037年,台灣成為美國的託管地,變成一個不死不活不好不壞的地方,在危機開始的第一刻,總統留下一篇文青式的告別宣言,就飛到到美國,台灣的小日子還是過的很好,沒有任何變動,這是一個詭異的作品。
〈陳冠中 盛世〉
作品在2009年人民共和國60周年紀念出版,講2013年全國經濟大恐慌,只有中國全民在共產黨領導下迎接盛世,經濟發達,生活美好,在這樣的時刻,人們得了一種輕飄飄的病,每天都快樂的不得了,忘記了所有記憶,只剩下官方的記憶,一切的一切如此平靜。地下抗議分子在2013年綁架領導人,領導人卻在一夜之間說服綁架者「我們必須這麼做」。
〈陳冠中 北京零公里〉
北京是一個血腥殺戮之城,鑄成偉大的天安門盛世,在北京,毛主席的屍體被完整封存,希望未來毛腦可以繼續領導人民,但他的腦袋早已被置換,引發一場毛腦爭奪戰。
〈陳春成 夜晚的潛水艇〉
不可思議的連鎖串聯了故事,在公元4867年,有一個紅學會成立在中國大地,紅樓夢早在20世紀成為禁書,直到兩千多年後有一個紅學黨,以研究紅樓夢為終生志業,紅樓夢成為一個暗號、隱語。
〈李銳 張馬丁的第八天〉
重新寫作了義和團在中國山西的教案,在1899年夏天,將近200多個中國教民和傳教士在一場教亂中被殺了,毓賢是當時的巡撫,艾士傑是大主教,殺了之後三天,傳教士需然又復活了,流落在山西的村落間,在飢寒交迫時在宋子娘娘廟前被一群女人收容,這些女人的丈夫在教亂中被殺,傳教士也和這些女子發展出恐怖而性感的故事。
〈馬家輝 龍頭鳳尾〉
1941年聖誕節,日本軍隊攻陷香港,是香港三年八個月淪陷的開始,馬家輝寫出這段被佔領時間的觀察,他以一個香港黑社會老大,在亂世中能繼續生存的有生存手段的人,在滿城都是漢奸的時代,這個黑老大愛上香港殖民官署的蘇格蘭警官,這是一個傾城之戀、斷背之戀,禁忌之戀。這個故事對應張愛玲的傾城之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蘇 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馬家輝將這個故事變成一個酷兒版的故事,似乎隱射了別的東西。
〈陳冠中 建豐二年〉
如果歷史再來一次,如果蔣介石贏了國共戰爭,歷史又會是怎樣呢?史達林把毛澤東流放到克里米亞島,蔣介石定都在南京,中國會發生甚麼樣的變化?也可能不會發生任何變化。建豐二年,1979年,蔣經國在南京做總統的第二年,聽到謀反的密報,交代楚瑜把抗議分子一網打盡。
〈吳明益 苦雨之地 〉
苦雨之地中充滿了讓人難以想像何以如何想像得這麼奇怪的故事,其中一篇「雲上兩千里」,描述一個作家戀上南大武山的雲豹,這個故事千變萬化,雪豹死了才變成故事,人變成故事就變成山的一部份,如果正經八百的說,這是一個關於生態、環境的後人類的故事,但是吳明益在骨子里強調了雲豹這個在19世紀才被發現的貓科生物,如何在20世紀迷惑了一個思念妻子的中年作家,作家把這個故事帶到山區,一切都如夢似幻,這個雲,是雲豹、雲上,是山里的雲霧繚繞,是情色的翻雲覆雨,充滿各式各樣的元素,也是雲端的虛擬性,苦雨之地架構在一個名為雲端裂隙的病毒,這個病毒會引誘你開啟記憶中最不願意碰觸的暗銷,讓人陷入,故事也一一展開。在故事的最高潮,雲豹出現了,在大武山一棵大樹的裂隙中,人和豹成就不可思議的因緣。
〈 夏曼藍波安 大海之眼 〉
夏曼藍波安是達悟族,提出了他自己對國家疆界的看法,國家是由海洋和土地構成的,「祖國」或國家認同沒有意義,我們的根就在大海裡面。在故事最高潮,作家來到南太平洋庫克群島,這個島和台灣差不多大,夏曼藍波安認為自己的先祖可能來過這個地方,這個地方使他終於可以認同,這也是台灣文學的包容性,夏曼的國族論述不應該被圈限在我們所熟知的本土論述裡。
〈駱以軍 匡超人〉
小說家的想像力到了我們無法招架的地步,匡超人描述駱以軍的私處破了一個洞,他用這個事件寫出了不可思議的太空大冒險,匡雞雞超人是受傷的,有個突兀的傷在凸出的部位,他想像這個傷口帶著淋巴液,有個機器在裡面挖呀挖的越挖越深,寫得絲絲入扣,把身體上的洞延伸成宇宙黑洞,發出了生命起源的大哉問,這個框架又連結到了儒林外史和西遊記,非常複雜的情節,也解放了小說的想像力,從身體到天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