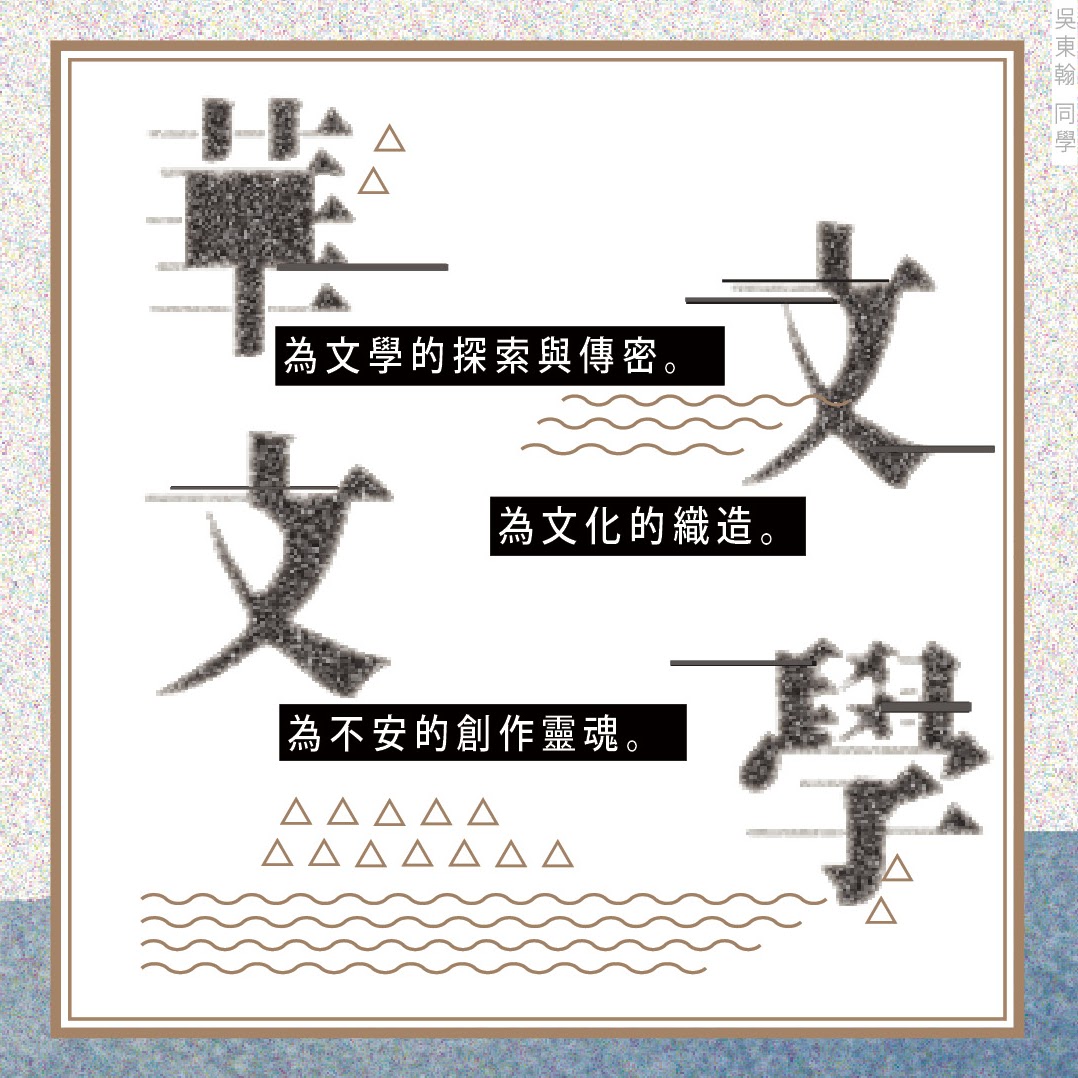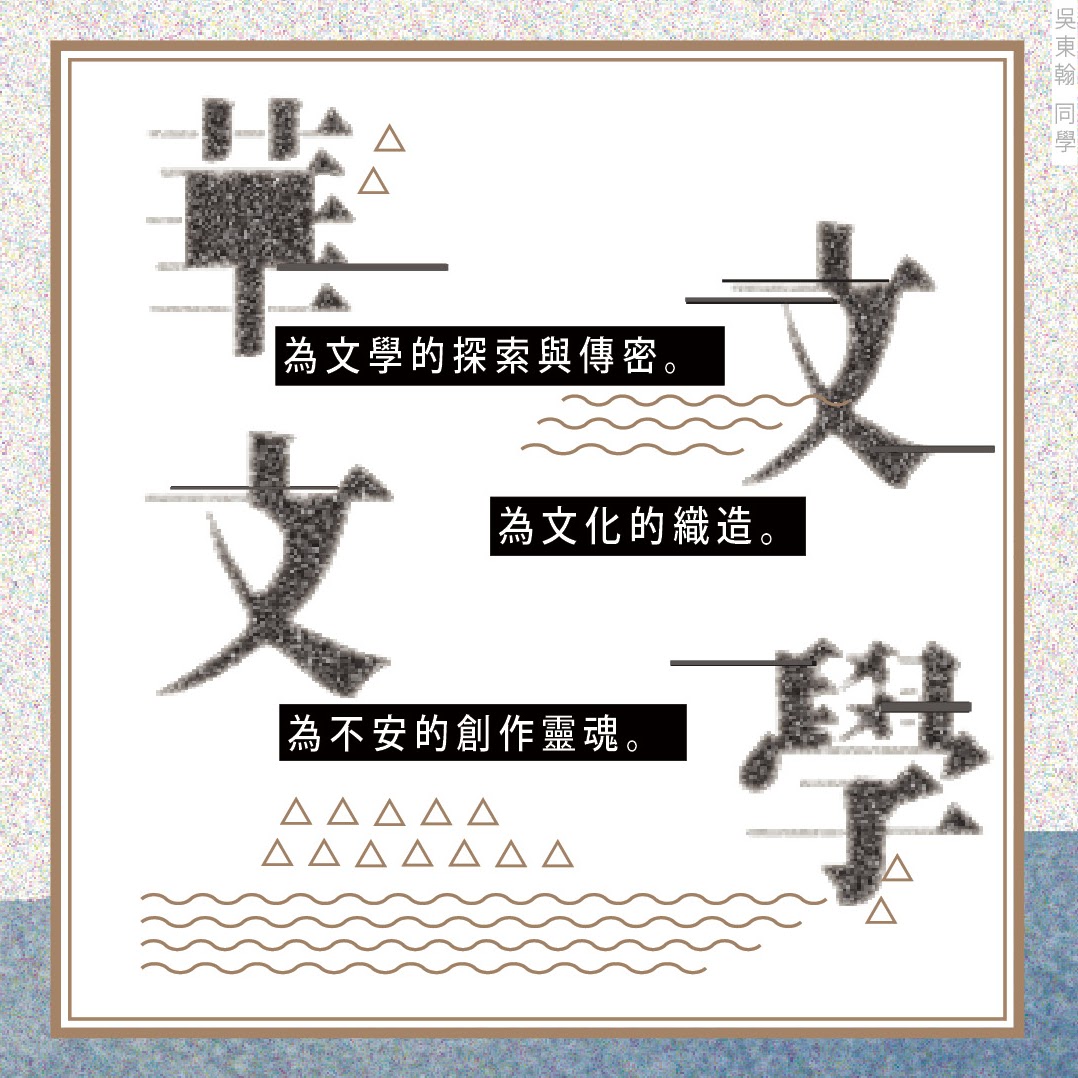主講人∣ 藍祖蔚老師
講題∣ 國家力量黑白春秋-兼論歷史記憶與電影再現
主持人∣ 李依倩老師
日期∣ 2022.10.03
地點∣ 人社二館第四講堂
【演講紀錄∣蔡宜芬】
30年前《捍衛戰士》上映後,引起美國年輕人從軍的風潮,究竟,看電影是一件什麼樣的活動?是娛樂、是消遣、是文化、是紀錄、還是一種傳承?
電影誕生於1895年,由法國盧米埃兄弟發明錄影技術,隔年,兄弟倆分派20位攝影師到世界各地,紀錄異國風土民情與景致,再回國將畫面展示給人們觀看,電影在最一開始,是一種傳遞知識的載體。再歷經幾年,蒙太奇在俄羅斯被發展出來,艾森斯坦認為,電影的魅力在於一個鏡頭跟一個鏡頭的剪接,前後鏡頭的連結產生出強烈的視覺碰撞,並傳達出訊息和符號。這是在共產體制底下,當權者將電影視為一種形塑國家認同重要武器而發展出來的重大進程。
到了二戰前夕,希特勒掌權的德國納粹也運用電影來操作民族情緒,影史上相當著名的《意志的勝利》出自一名女導演,萊芬斯坦,她不僅將艾森斯坦發明的蒙太奇用得淋漓盡致,更運用鏡頭語言中放大、仰角等方式來激起民族團結的情緒。
電影並不只是單純的娛樂,也是一種洗腦的武器。在了解政治歷史以及電影發展歷史,必須對此有理解認識。經典電影《新天堂樂園》劇情便展示出早期的審查制度,情慾與違反政治意識形態立場的內容不得播出。什麼事情可以看?什麼事情不可以看?掌控國家的人擁有決定權。
過去,國民黨極權統治底下的台灣,審查由文化部執行,電影由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影)製作,在那個時代,統一由國家決定人民可以看什麼內容。
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成為國際孤兒的社會氛圍底下,學校帶領全校師生欣賞撫慰人心的軍教電影《英烈千秋》、《梅花》、《八百壯士》,這些電影都在告訴人民,雖然遭遇挫敗,但人們應該要懷抱壯志,戰敗也要有戰敗的壯烈。這幾部電影皆由中影製作,動用國家資源與經費,拍攝出大場面的製作。當時,國民黨是帶領台灣前進的重要政治領導力,但在鞏固政權的過程中,往往也做出違背人道的行為,像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白色恐怖。
在極權的統治底下,台灣電影走入健康寫實主義時期,《養鴨人家》、《蚵女》等以寫實為基調,可以在電影中看見當下活生生的景象,但是寫實前面加了健康二字,意思其實就是,我有政治的期許,我只讓你看見光鮮美好的一面。
中影,有其時代記憶影像的意義,不是刻意的,而是他們拍攝下來的影像剛好紀錄整個時代,到底當時台灣長成什麼模樣?爸爸、媽媽或者是爺爺、奶奶走過的歲月,就這麼被中影忠實紀錄下來。
1982年,出現一群出色的年輕人,開啟了台灣新電影時代,這群年輕人以最貼近台灣的社會樣貌拍攝電影,完全不同於過去的創作風格,內容皆是取材自台灣本土的故事,楊德倉、侯孝賢、蔡明亮、李安、李屏賓、杜篤之、廖慶松等大師,正是在此誕生。當時電影《兒子的大玩偶》裡頭真實呈現出台灣人的落後與貧窮,被中央電影公司要求修剪,電影史上稱之為削蘋果事件,當年的聯合報記者楊士琪,相當具有勇氣的將萬仁導演提供的資料一一報導出來,在爭取獨立創作空間的堅持下,終於獲得只要修剪一小刀即可上映的局面。楊士琪女士在兩年後因氣喘病發離世,現在設立有台北電影獎楊士琪卓越貢獻獎、傑出影視廳工作者楊士琪紀念獎。
1989年,台灣新電影走上另一個高峰,侯孝賢導演所拍攝的《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拿下大獎,那是在台灣剛剛解嚴的年代,內容已經觸及過去50年都不敢碰觸的議題,也就是228歷史傷痛的記憶。
當台灣電影發展到國家干預減少到只提供分級的參考,緊接著要面對的,是外國勢力的入侵。1998年政府加入 WTO,全面開放外片進入台灣的電影院。在過去,一部外片只能有四個拷貝,因此提供台灣電影充沛的創作能量,然而,在開放外片之後,台灣拍電影的人越來越少,國家輔導金制度隨之出現。輔導金的原意是負擔拍攝費用的三分之一,不過在窘困的拍攝環境下,創作者將三分之一的輔導金當成全部的經費,影響了創作品質,這是為何輔導金為人詬病的原因。台灣電影製作走過一段相當低沉的歲月,但是平心而論,李安、蔡明亮等諸位導演,在年輕時也歷經輔導金的資助,有過去的經歷,才有今天的累積。
而後,公共電視成立,製作有別於商業電視台具有教育意義或藝術性質的電視節目,應該擁有獨立創作空間的公共電視台,仍舊夾在政黨權力意識形態鬥爭之間,立委會要求公共電視的人事安排、預算多寡,來符合執政黨的意念。即便到了今天,媒體依舊是政治必爭之地。
近幾年,串流平台興起,台灣也成立Taiwan plus,國家希望比照韓國影視在國際上的力量,期許透過Taiwan plus向外宣傳台灣正面價值。電影或是影像作品走入國際已是趨勢,2014年馬丁史柯西斯帶著團隊來到台灣拍攝《沈默》,拍攝進行到一半時,馬丁想要看看已經拍攝下來的毛片,於是請求當時的國家電影中心協助,當時國影中心馬上拒絕了,因為即便是頂著堂堂國家的名號,卻完全沒有一個能好好播映毛片的設備。也許在此刺激下,國影中心重整,國家編列預算,開始修復過去的電影膠片,保藏台灣的歷史。
有記憶,才可以說故事。
但是,歷史有歷史的弔詭。美國曾經拍過一部電影《西部開拓史》,這是一部在白人觀點底下的視角,取得原住民的土地是一種贏得、是一種勝利。回頭看看台灣原住民,一開始漢人對於他們的無知與誤解普遍存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1950《吳鳳傳奇》穿著紅衣服、犧牲自己性命來取得原住民認同,都是以殖民者的視角觀看。《莎韻之鐘》也是殖民觀點底下用來宣傳理番政策的成功。原住民怎麼樣看待這樣的電影呢?
時代轉換後,《海角七號》、《KANO》、《好男好女》等電影又帶出不同觀點的歷史詮釋。直至今天,台灣電影產業上加入許多原住民籍的導演,像是2022年入圍金馬獎的陳潔瑤,他們以原住民的角度出發,講述自己的觀點、自己的故事。
歷史重新搬演,透過影像聲音,虛實辯證歷史事實,這是在重新詮釋過去時,期許可以做到的事。
【演講紀錄∣劉大芸】
|影像的魔法
政治人物意識到電影敘事的魔法,便開始利用影像動員、進行政治洗腦。希特勒在《意志的勝利》中運用影像傳達「日耳曼的力量」;電影的魅力在於一個鏡頭跟一個鏡頭的剪接,僅僅一個仰角alexander nevsky 就可以造就國族英雄;俄國人在視覺結合聽覺的震撼下,陶醉於政治氣氛中甘於接受國家的指揮。
政府餵養人民、決定人民可以看什麼:
政治宣傳:1896年(電影誕生的第二年),電影巡迴世界,每一部商業影片放映前有三分鐘的世界奇觀介紹。這是美國的對外宣傳,歐洲與亞州隨後跟進。
《新天堂樂園》:片中負責審查影片的牧師會在所有不適合的地方搖鈴,代表必須刪除,當藝術創作奮勇向前時,會有一群人告訴群眾說「這些畫面是不適合你看見的」,而這部電影最後的五分鐘便是歷史上所有被剪掉的激吻的畫面,向那個保守荒謬的時代致敬。
台灣:政府(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核發的電影檢查准演執照決定
人民看什麼,現在是按照年齡分級,過去則依據內容審查。
|削蘋果事件
國民黨文化工作會對《兒子的大玩偶》下令修剪,甚至禁演令,記者楊士琪用頭版頭條對其嚴厲批判。
楊士琪紀念獎:黨意之外,還有更該追求與堅持的理想。在保守的環境下長大的人仍然能在某些情境下做出符合自己理想的作為,在這樣的情境下更能體現出人的作為。明驥受獎被稱為:「這並不是一個官高權重的人所能享有的敬重」。
《悲情城市》:處理二二八的禁忌議題,是那個時代的凝視。梁朝偉飾演的啞巴男主角無法用語言溝通,並不是個人的殘疾,而是整個時代的失語——而文字最終是勝過語言的。解嚴之前我們致力於批判、打倒威權,而如今又要如何重新凝視過去的歷史與政治傷口?
公共電視:當有權力的人靠近媒體時都難免希望媒體對自己有好感,公共電視便是商業體制之外的公共服務。其禁止政治人物干預、一年只有九億經費且逐年遞減且不能播新聞。
|國家電影中心
「當你們走進國家電影中心的片庫時,會聞到一股你們從前都沒有聞過的味道,而一旦聞過,以後也很難忘掉。那是膠片釋出醋酸所散發的酸腐味,這代表膠片隨著歲月風化,正在逐步邁入死亡。那是正在消失的記憶的氣味,讓我想到侏羅紀公園中那隻琥珀裡的蚊子。」
國家電影中心的宗旨是保存、典藏過去,守護昨天、指向明天。低溫片庫的工作同仁們在做的是與時間賽跑,拯救那些凋亡中的電影,其中很多都可以揭開過去台灣電影不為人知的神秘面紗,只是逐漸鏽蝕中。
我想到正在讀的安東尼.馬拉小說《我們一無所有》,審查員將被政治處刑的弟弟的臉從照片中塗去,卻又為了姪子再將其畫入一幅幅畫作中。人類好像都走在同一條荒謬的路上——先是拼命地刪除,接著又拼命的復原。試著挽救些什麼。
「他打算轉頭,但我喝止。『你直視前方。油畫裡的人們不可以轉頭看看
誰在他們身後,你也不可以。』
『我看不到幾隻指頭,』他說。『你的手移到太後面。』
『沒錯,』我說。『那裡就是你爸爸所在之處。他被畫入背景之中,隱身
在你腦袋瓜後面一個你看不到的地方。他在那裡。但你永遠不能回頭望。』
銅板的刮擦聲早已停歇。當我抬頭一望,男孩的媽媽已經站在臥室門口。
我跟著她走進臥室,照片整整齊齊地排列在桌上,每一張照片都有一個人的臉孔被狠狠刮除,下手之重,木桌的紋路甚至明顯印蝕在空洞之處。我看在眼裡,心頭一陣刺痛,不禁閉上雙眼。」——安東尼.馬拉《我們一無所有》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