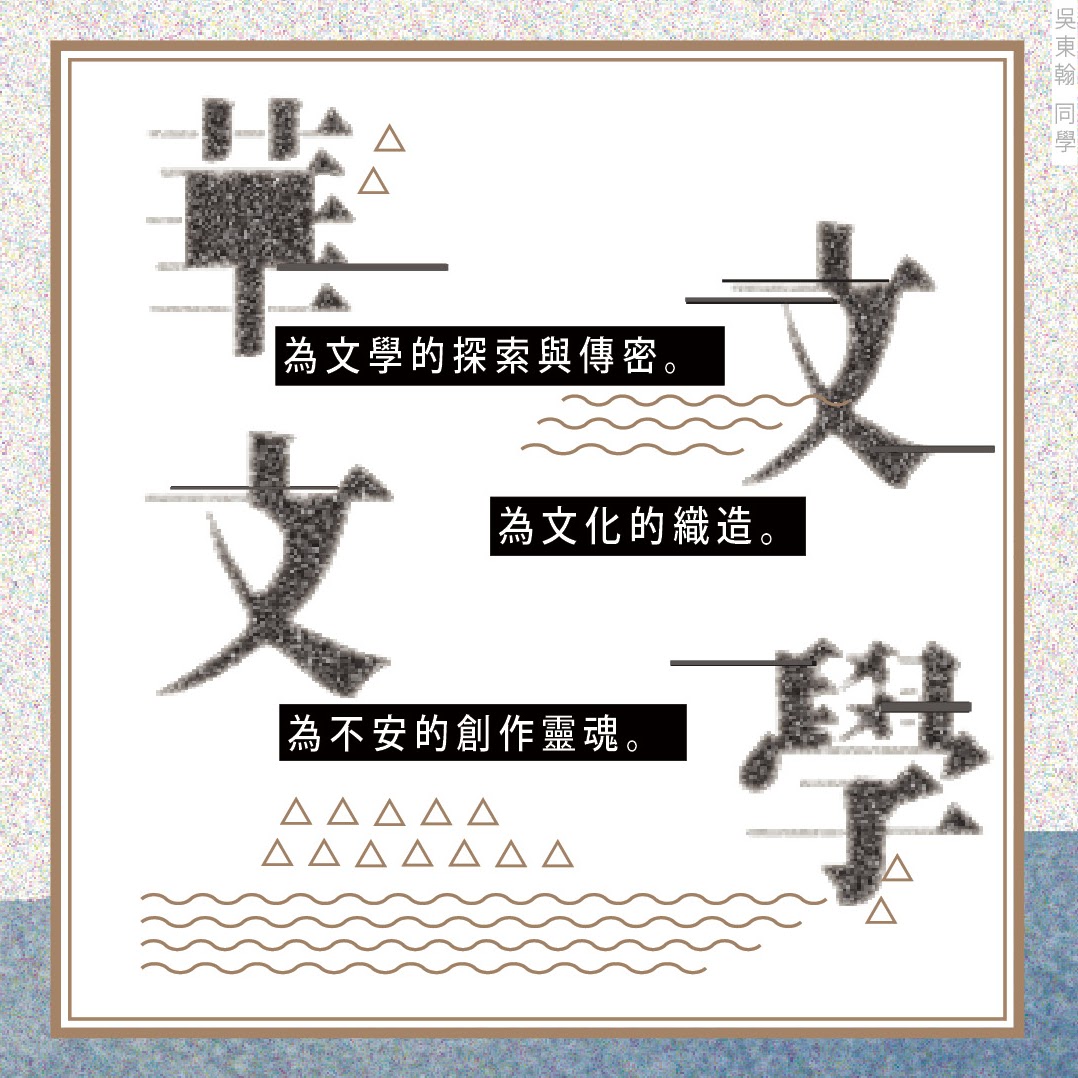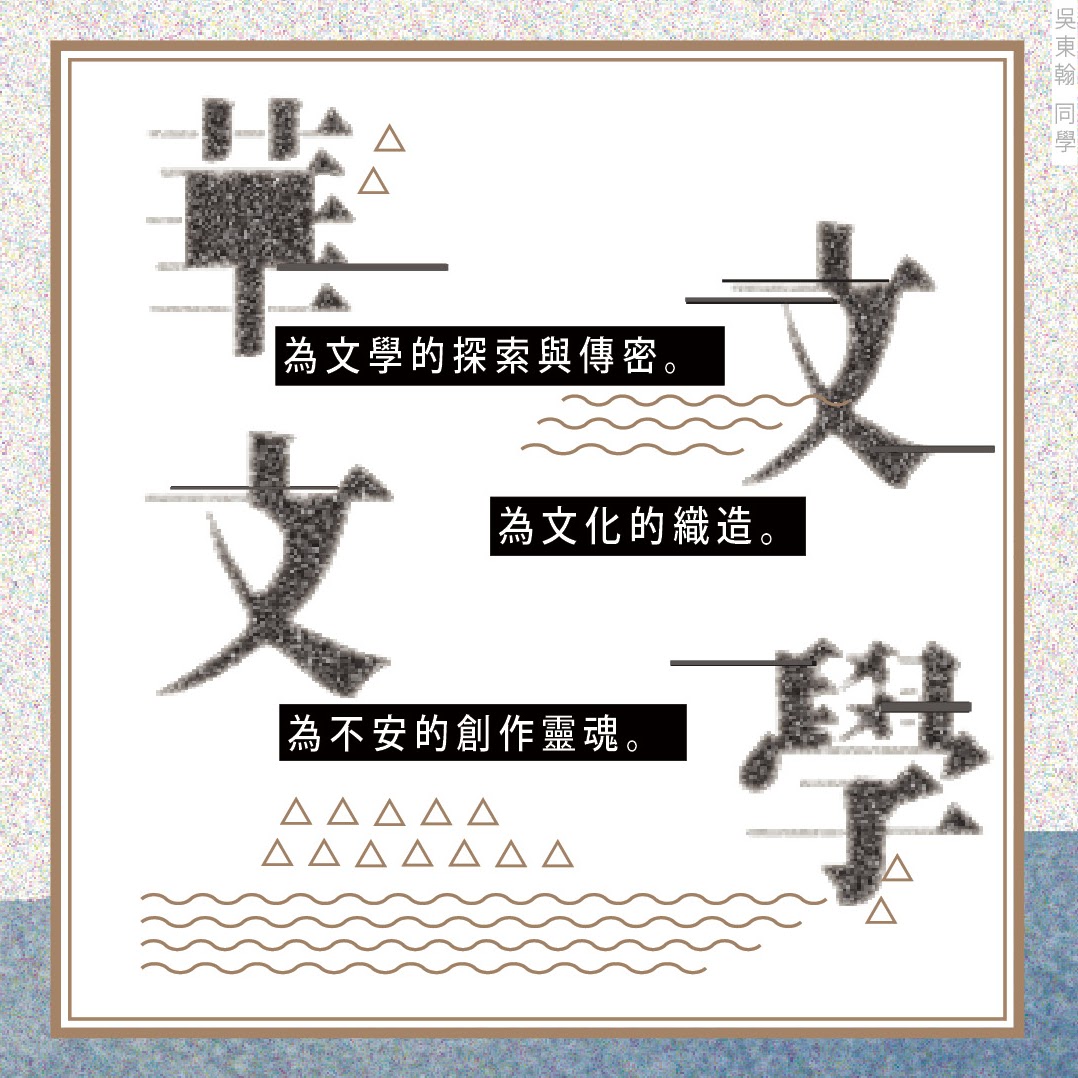主講人∣ 沙力浪老師
講題∣ 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報導書寫
主持人∣ 張寶云老師
日期∣ 2022.05.20
地點∣ Google Meet 線上演講
【演講心得∣劉清華】
沙力浪老師分享了他文學創作的歷程,轉變和初心,其中他提到創作是為了保存布農族的文化和漢語族語書寫之矛盾最令人深刻。老師從其早輩,布農族人怎樣被日本人迫遷,由南投搬到花蓮,說到部落的地名也是日語與族語混合等等的歷史背景,由此想到近百年被受關注的「離散」(diaspora)書寫。因著戰爭、殖民主義、帝國軍事主義、國家主義⋯⋯世界上不同部落,人民的土地因而喪失,流離失所。當「大歷史」成為主調,個人論述經常在當代文化中缺席,沙力浪老師提醒我們書寫個人/部落歷史的重要性。老師將其在部落成長,到融入主流體制中的矛盾、困難和失落都寫進文學作品之中、保存和紀錄族語,把族語混入漢語書創作、將部落神話故事寫入詩裡、反思殖民期間之衝突等等⋯⋯個人的生命故事即使微少卻能深刻地用文學創作保存下來。
老師也談到由創作詩到書寫報導文學的轉變,不同的創作媒體提供不同的功能和面向,想起Virginia Woolf在《如何閱讀一本書?》中提出詩、小說、傳記本質之不同(時間性,結構,與讀者的關係、真實性等等)。沙力朗老師再細緻分析了新聞和報導文學之分別,後者強調人物和空間描寫,補充故事的細節和脈落等等。
【演講心得∣鄭雯玲】
這次講座,講者沙力浪老師先從自己寫詩的經驗談起,身為布農族的孩子,打小生長在族語環繞的世界裡,一直到他開始上學接受主流社會教育之後,不得不以中文書寫、思考,這使得他產生了一種失落感。因此在大學一年級時寫出〈笛娜的話〉(笛娜在布農族語意指母親)一詩來抒發這種失落感,並進而產生想要找回失落的族語的文化關懷:「重新說出笛娜的話」。漸漸地,他開始以中文書寫和部落文化融合的創作,比如〈穿釘鞋的日子〉,這同時也是他開始在主流社會中尋找身份認同的時期;〈尋找鹽巴〉一詩中以鹽巴象徵失去的「原味」的身份;〈部落描寫〉書寫部落耆老裡的織女的故事。並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部落的燈火》。
在尋找和書寫的過程中,他逐漸發覺,詩這個文類過於精煉,不能完全涵括他所想要保留與傳承的部落神話和民俗文化,於是他轉向報導文學的寫作,並且和部落長輩進入山林,以沙力浪老師的說法是:「進入祖靈的知識」。他回到部落之後,和部落的長輩一起入山,對部落的遷移歷史和清領、日治時期的布農族歷史進行研究、口傳文學的訪談,除了為保存族語的目的以外,也藉由重新認識山林的身體經驗、長輩傳承的歷史,將自己和陌生的山林空間連結在一起,建立起布農族面對山林的態度。
在沙力浪老師轉往報導文學寫作後的第二本書《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詳細描述了清領、日治時期的族人作為揹工的生活環境,並藉由族語和中文兩種語言的交錯互寫的形式來寫作本書。沙力浪老師在石板屋的歷史重建現場擔任紀錄員,提到自己也背了一塊石板。
寫作契機是從一張黑白的揹工群照,沙力浪老師從這點開始重新審視過往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布農族人。比如日人無法理解布農族人會視山林情況而改變行進速度,這點和有時程計畫的日人觀念相衝突。沙力浪老師書寫這本書的用意其一便是為了向讀者述說族人自身有對山林的理解和知識,比如有捕獵到充足食糧,山林就是安全的,而非如日人記述中那樣隨意不按時程表休息的懶散形象。
在報導文學的寫作裡,沙力浪老師提到報導文學除了必須要有歷史性的回顧,也要有對於事件的未來性有所瞻望,比如重建過後的石板屋如何妥善保存?有無可能結合現代科技來達到讓更多人認識的目的?⋯⋯等等問題。沙力浪老師以豐富的生命歷程結合書寫經驗,給聽眾帶來富有生命力的報導文學講座。
【演講心得∣李修慧】
在這學期這麼多不同領域的作家分享中,最讓我心有戚戚的,是布農族作家沙力浪對於文體的分析。講座中,沙力浪跟我們分享了他從寫詩,逐漸轉向報導文學的心路歷程。
沙力浪大學時讀中文系,接觸了文學後開始寫詩,當時他的作品雖然帶有一點族群意識,但多數作品還是以個人感懷為主,詩中也充滿象徵、意象。後來,他到了東華大學就讀民族發展所,開始對族群理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讀越多理論,就越感覺到文學的「無力」,於是沙力浪開始疑惑:詩真的能夠改變族群的命運嗎?他甚至開始思考自己是不是要擺脫詩。
最終,沙力浪沒有放棄文學。但他確實離開了新詩創作,轉向另一種文體。如果說,每個文本都是承載內容的容器,那麼,不同的文體就像不同形狀的杯碗瓢盆,適合不同的內容物。沙力浪指出,詩是一種相對精煉的語言,對於族群故事跟族群文化的存續、記錄,幫助比較小,因此,他開始轉而創作報導文學,對他來說,他想結合文學與理論,而報導文學是最適合的容器。
沙力浪對於文體的思索,也是我常常思考的問題。身為現代詩的創作者,我也常疑惑現代詩是否有能力承載當代的訊息。
剛入學時,我一直想把我最重視的「性別議題」跟我想創作的文類「現代詩」做結合,可是實際操演後,我發現一旦我想要書寫的議題「太當代」,讀者就很難理解。而創作又是一門這麼荒頹孤獨的路,有時候你很難確知,究竟是自己才華有限、火侯不夠?還是這個議題真的太少人懂?
後來我開始學會等,例如近五年才開始被廣泛討論的 deepfake 犯罪的議題,我從三年前就開始研究,但直到去年「小玉換臉」的新聞引起廣泛的關注,我才感受到「寫 deepfake 的時機到了」。也正好是在這時,我逐漸學會抽開一點距離去寫議題,多留一些空間給文學性,也是在這個時候,讀者才開始能理解我要寫的內容是什麼。我的目標「結合當代性別議題與現代詩」才終於有了小小的成就。
而沙力浪面對的,是比性別議題更弱勢的族群文化,臺灣許多族的語言都已被列入瀕危、部落人口流失的狀態還在持續,他所感受到的焦慮一定比我更深刻。而報導文學一直到近幾年,才普遍被文學圈的人所接受(沙力浪的報導文學作品也直到 2019 年才出版)雖然沙力浪的作為,看起來很像現代詩的逃兵,但或許,為適合的主題找到適合的文體、事宜的時機,才是對文學更純粹的忠誠。
【演講心得∣陳愷蓮】
「我努力尋找風的蹤跡,卻看不到風的顏色,聽不到風的聲音。」第一次知曉沙力浪,是因為《走風的人》,在《祖居地・部落・人》的這首詩中,我感受到了一個離開部落的人對山林的迷惘與哀愁。去年課上籌辦展覽時,同學們有幸邀請到沙力浪老師舉辦了一場走讀活動,實際走了一趟瓦拉米步道,雖然我沒參與到那段路程,但看著同學們的紀錄影片,總能感受到山林的雄偉與壯麗。
沙力浪在上了大學後離開部落到平地唸書,也是因為這段經歷,他開始尋找自我,運用族語創作,讓更多人認識部落的文化,為原住民所面臨的問題發聲。而大哥是引導他的重要人物,透過大哥述說族人們與山的故事,他說:「大哥把山介紹給我,也把我介紹給山。」他跟著他大哥越過高山,回到他們的祖居地,感受到自己與山林間有著深深的連結,之後更成為了高山協作員,從此與山密不可分。
在《用頭帶背起一座山》中,印象深刻的是老師對頭帶的講解。頭帶是族人的智慧,在登山時具有比登山揹包更多的功能,是布農族人不可或缺的重要之物,老師說:「頭帶戴久了,就會符合自己的頭型。」頭帶陪伴著族人們一次次走入山林,帶著族人探尋祖先的走過的路,如同在《部落的燈火》中所寫的:「獵人的腳印,不是要帶我去登山,而是認識祖先的路。」在老師的筆下,我們總能看見他在追隨前人的腳步之中,留下屬於自己的腳印,帶領更多人認識部落與山林。